摘要:明治初年,為了從精神上統一國民,明治政府開展了由神、佛共同承擔的國民教化運動。在此過程中,神佛雙方圍繞作為“宣教教材”的“三條教則”產生了種種紛爭。這些紛爭不僅導致國民教化運動失敗,還使神道的宗教特質被抽離,成為一種“非宗教”的存在,即產生了所謂的“神道非宗教”理論。而這一理論又預示了神道之后的走向,為“非宗教”性質的國家神道之成立開辟了道路。
關鍵詞:三條教則;國民教化運動;神佛紛爭;神道非宗教;國家神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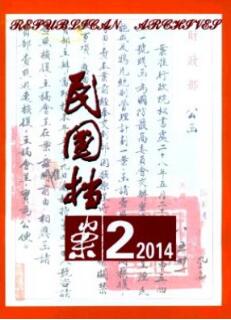
《民國檔案》(季刊)創刊于1984年,是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主辦的一個刊載民國檔案史料兼為民國史研究提供園地的刊物。
引言
自明治政府成立之日起,便制定了以神道教化國民的基本路線,在其推進過程中,又采取了壓制佛教、禁止基督教傳播等措施,引發了各宗教人群的極度不滿以及國際社會的強烈抗議。面對這一情勢,政府于1872年設置了統管神、儒、佛等諸教事務的教部省,改由各教協同教化民眾。教部省雖在政策形式上采取“神佛合同(平等)”的策略,但其實質依然以神道為重,意圖集各宗教之力,防御基督教,最終達到神道國教化之目的。然而,由神佛雙方“合力”開展的國民教化運動,非但沒有達到政府預想之結果,反而使神道原本擁有的宗教特質被抽離,成為一種“非宗教”的存在,進而為國家神道的成立開辟了道路。這一結果的產生,無疑與國民教化運動中神佛雙方的“合作情況”有著重要聯系。關于這一方面的研究,有學者著眼于國民教化運動的過程去探討,指出國民教化運動內部神道與佛教紛爭不斷[1]95,神道在教義、布教技術、組織等方面暴露出其脆弱之處,神官教導職雖在形式上握有教化的主導權,但實際上卻依附于佛教[2]10。也有學者聚焦于國民教化運動的結果,認為正是由于佛教諸宗不愿在教化運動中放棄自身教義,為避免使自身教義之宣傳受到限制,而最終退出大教院,停止了“合同”布教[3]325。無論著眼于過程亦或是聚焦于結果,上述研究均未對神佛雙方由統一對外(防御基督教)到分道揚鑣過程中出現的具體紛爭以及由此暴露的神道方存在的不足作深入探討。本文以國民教化運動中作為神佛雙方共同“宣教教材”的“三條教則”為中心進行考察,從以下三個層面展開分析:首先,“三條教則”成立過程中神佛雙方產生了怎樣的紛爭以及神道受到了怎樣的沖擊?其次,“三條教則”頒布后,神佛雙方圍繞“神”概念的解釋又出現了怎樣的紛爭并暴露出神道的哪些不足?再者,由“三條教則”引發的一系列紛爭對神道之后的走向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日本思想史上的神佛關系專題——以“三條教則”為中心
日本問題研究2019年第5期一、“三條教則”誕生的歷史背景
1868年3月,明治政府發布“祭政一致”的布告,其中稱:“此次王政復古,根據神武創業之基,諸事一新,恢復祭政一致制度。首先恢復、建立神祇官,然后陸續興辦諸種祭奠……”[4]425這一布告明確指出恢復“祭政一致”制度的具體措施包括恢復、建立神祇官一職。隨之,1869年7月,明治政府通過官制改革將神祇官置于太政官之上,確立了其在政府機構內的最高地位。1870年1月,明治政府又以天皇名義發布《宣布大教詔》,該詔旨在將神道置于“大教”的位置上,詔書中說:
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極垂統,列皇相承,繼之述之。祭政一致,億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風俗美于下。而中世以后,時有污隆,道有顯晦。茲者天運循環,百度維新。宜明治教,以宣揚惟神之大道也。因此新命宣教使,布教于天下,汝群臣眾庶,其體斯旨![1]81
該詔闡明了重新宣布大教于國民的意義與目的,即“治教”為歷來之傳統,然而中世以后,受到破壞,如今萬事一新之際,應明確治教,以宣揚“惟神之大道”“治教”是指與政事相關的教化;“惟神之大道”中“惟神”一詞出自中國《晉書》,意為“依神之意,毫無個人之念”。日本自江戶時代起便將“惟神之大道”作為神道的代名詞而使用。 。由此,政府向各地派遣宣教使“宣教使”是明治政府為防御基督教,向國民宣揚天皇親政體制,于1869年9月在神祇官下設置的教化國民的職位。,開始布教。1871年,明治政府下令社寺領地由國家管轄,并制定神社社格,新訂氏子調查制度氏子調查制度是從宗教方面來管理國民戶籍的制度,其目的在于使神社參與戶籍的編制和管理,由神社來控制作為氏子的日本全體國民。例如,其中第一條規定:臣民如生嬰兒,應向戶長報告,并參拜神社,領取神之護符。,實施了一系列樹立神道為國教的措施,將神道國教化政策推至頂點[2]6。
與此同時,明治政府采取了分離神佛的態勢。1868年3月,太政官發布《神佛不可混淆令》,命“以佛像為神體之神社,須從速改換”,“懸掛于神社前的佛像或者金鼓、梵鐘、佛具等,須盡快拆除”[4]425。同時,還采取多項措施,使皇室、皇族與佛教脫離關系。政府推行神佛分離的本意是想突出神道,將其樹立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但由于地方未能恰當理解新政宗旨,許多人把“神佛分離”理解為“廢佛毀釋”,從而形成了一股排佛之風,大量堂舍、經卷、佛像被毀,僧侶被歐打等暴力事件也屢有發生。由此招致佛教界的各種不滿甚至暴動。
在壓制佛教的同時,明治政府延續了幕府時期的基督教對策。1868年3月,樹立告示牌禁止基督教傳播。并在處理日漸增多的基督教徒問題上,表現出較為強硬的態度,分批分次將不加悔悟的信徒流放至其他各藩,引起了外國公使的強烈抗議。
面對神道國教化政策推行過程中遇到的眾多阻力,“明治政府決策層開始對神道一元化政策進行反省,認識到要維護神道國教化和加速推進國民教化,必須實行較為寬松的宗教政策。”[3]3201871年8月,神祇官被降格為神祇省,其中擔任要職的平田派國學者由于所主張的“祭政一致”政體施行困難,多數被排除在神祇省之外。政府清楚地認識到國民教化運動如果沒有佛教方的合作,僅靠缺乏布教經驗的神官宣教者將難以推行[5]5。于是,1872年3月,明治政府宣布廢除神祇省,設置教部省,由神佛“合力”承擔國民教化之責,取代從前的宣教使,設置教導職,主要由神官和僧侶來擔任,此外,還采取教導職擴大到志愿人士的方針,民間宗教的傳教者自不待言,區長等基層統治階層以及評書演員、相聲演員,凡是能說會道的,均可充當教導職[1]93。作為各教導職教導民眾之指南,教部省于同年4月頒布了“三條教則”。
二、“三條教則”成立過程中
的神佛紛爭在明治初年推行神道一元化的環境下,設置教部省、允許神佛“合同”布教,無疑是明治政府在宗教政策方面做出的一項柔性措施。那么,在這一措施達成前夕,神佛雙方各自抱持怎樣的目的,又分別采取了怎樣的舉措?“三條教則”的頒布使雙方產生了怎樣的紛爭,對神道的地位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一)“三條教則”頒布前神佛雙方之目的
1870年10月,太政官在民部省內設置寺院寮,佛教地位逐漸趨于穩定。在此背景下,以島地默雷島地默雷(1828-1911)出生于周防國佐波郡的西本愿寺,之后成為同郡妙誓寺主持。1868年進京參與規劃本山寺院的改革,為西本愿寺派改革的中心人物。島地確信真宗具有近代性,并對日本的近代化具有強烈的使命感,提倡“信教自由”論,在明治宗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為首的佛教方主張借國家權力之手,建立使寺院、僧侶能夠參與其中的教化體系和教化機構[4]231。1871年7月,太政官令宣布“大教宣布之事”,要求對基督教保持警戒。以此為契機、島地默雷于同年9月向政府提出建議:
臣以為,今人猶有防邪之志,今民猶染佛教之習。朝廷若明應信此教,使其盡防邪之職,望可免于滔滔之患……臣是以請,換宣教之官(神祇官),更以總管教義之一官,管寺院督僧侶,自不待言。凡天下,無不為教管制之處,無不為教督正之所,而除以專恣雜亂傷國體、妨朝政之害,庶幾可至上下情齊,政教相扶之域。[6]89
他指出,佛教參與教化運動的目的在于防御邪教(即基督教),并從“政教相依”的立場出發,懇請政府取消神祇官(此時已降格為“神祇省”),設置一個管理寺院、監督僧侶的官職,以使國體、朝政免受侵害。基于佛教的政治活動與神道教化不力等現實情況的考慮,1871年10月,太政官咨詢機構左院向正院提出《寺院省設置建議》,其部分內容引用如下:
邪宗之儀所謂教化使然,若侵入至深,防之亦非教化不可。若任由其發展,佛教衰亡,基督教逐漸盛行,至議論共和政治亦不可知。宣教使、佛徒均應盡力,因此如今設立寺院省,立以下之目的,諸宗相奉,教化人民……[7]21
該建議雖旨在防御基督教,但其中內含著佛教欲設置獨立一省(寺院省),以與神道的神祇省對等,并進行單獨布教的政治意圖。這一時期,在宗教管理方面,因涉及條約改正問題,日本政府遭受了外國施加的“信教自由”之壓力,社會籠罩著對基督教之侵襲的恐懼。因此,從政府的立場來看,與其成立一個與神祇省同等級別的寺院省,由佛教單獨布教,不如神佛“合同”說教以防御基督教更加強力有效[8]1062。于是,該建議被駁回。但在佛教的繼續活動下,兩個月后,左院再次提出建議,但這次不是設置與神祇省相對等的機構,由佛教單獨布教,而是設置能統管神、儒、佛各教事務的教部省,集各教之力,共同開展國民教化。建議書中這樣說到:
置教部省,總管歷來諸教事務。神道及儒佛各置教正,教育信徒,善導人民。中外教門甚多,取舍其正邪至為重要。然遵奉宗教,乞托一家一身乃是彼我皆難免之民情。故,若有違反我政府制定之法律之宗教,應有權斷然予以制裁。[3]320
由于此建議與政府意圖一致,隨即被批準,并于1872年廢除神祇省,設置統管神、儒、佛諸教事務的教部省。
從島地默雷的提議以及《寺院省設置建議》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佛教以挽回勢力,獲取與神道同等地位為最大目標。與此相對,幾乎在同一時間(1871年11月),以田中賴庸、山之內時習二者均為當時神祇省的核心人物。為代表的神道方向西鄉隆盛等參議聯名上呈了《獻議》,其中這樣寫到:
西洋各國之勢,日滋月益,極奇技長器之巧,挾耶穌教,加之以兵威相迫,天地開辟以來,如此大難尚未有之,況洋學者,主張共和政治……神祇耶穌兩教,決不能并立,興神祇自去耶穌之害,不去耶穌之害,神祇之道自廢,出甲入乙,其間不容毫發,況興神祇之道至難,去耶穌之害不易,然若不傾注萬千精力,盡多種方法興神祇之道,耶穌之害會與日俱增,腹心之病難以平愈。[7]28
與佛教的意圖不同,這一時期的神道視基督教為心腹大患,欲傾注全部精力,利用一切方法對其進行抵御。神祇省官員常世長胤在《神教組織物語》《神教組織物語》分上中下三卷,是1885年常世長胤向門人口述其回想的筆記。記錄了從1869年設置宣教使到1885年廢除神佛教導職期間,宣教使和教導職的具體活動內容。中說,1871年12月,“神祇省和宣教使逐漸衰亡,如同將死之人仍在喘息一般。”[7]29若以此為教部省改組前神祇省之實情,可以說神道方在如此自顧不暇之際,會對政府設置教部省目的的關心更大程度地集中在防御基督教上。
(二)“三條教則”之內容與補充
教部省成立后,第一個舉措便是頒布國民教化的總綱領——“三條教則”,以確保大教宣布運動的嚴肅性與統一性。其內容包括:(1)應體察敬神愛國之旨;(2)應明天理人道;(3)奉戴皇上,遵守朝旨[9]66。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