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電影成為當代主流文化消費的藝術之一,有關怎樣的電影能被稱作經(jīng)典藝術的發(fā)問反復出現(xiàn)。劉恒關于電影的本體論、創(chuàng)作論和電影人論提供了一種可謂清晰而辯證的思路。他提出十五組反義詞,發(fā)掘電影的政治、社會和藝術等多重力量;兼顧電影的藝術性和商業(yè)性,提升了商業(yè)電影、大眾電影的藝術地位。他的電影創(chuàng)作論,為青年導演提出了對電影的新的想象,并且為電影創(chuàng)作的實際落地提出了可行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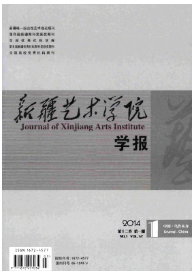
李晶, 新疆藝術學院學報 發(fā)表時間:2021-09-03
關鍵詞:劉恒 電影 藝術的力量 本體論 創(chuàng)作論 電影人論
一、電影的多元力量
語言是人類存在的方式,具體而言,口語、書面語、圖像……都是語言的表達形式,也是人存在于世界的多種方式。通過文字,文學書寫詩意,講述故事;運用線條、色彩,繪畫描述世界,表達情緒;組合畫面和聲音,電影以銀幕呈現(xiàn)世界,傳達情感。劉恒認為,在表達相同內容的時候,選擇的語言表達形式不同,最后產(chǎn)生的效果具有差異性①,而效果差異的背后,實際上是由不同語言表現(xiàn)方式的不同力量所決定的。圍繞電影的效果來說,劉恒指出電影的效果,展示出電影的力量;電影的力量包含三個部分,分別是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藝術力量。
電影作為文化政治博弈,其政治力量展現(xiàn)出,從國家競爭到人類創(chuàng)造的遞增。在電影的三個力量中,政治力量位居首位。當前國際社會,最鮮明的表征就是國與國之間的博弈,博弈并非由單一因素決定,而是融合政治、軍事、經(jīng)濟、外交等,構成國家間的立體博弈,文化也屬于綜合立體博弈的一部分,電影作為文化政治博弈的一部分,承擔了鞏固國家安全與豐富人類創(chuàng)造成果的使命。一是守衛(wèi)使命,對外來意識形態(tài)及文化的甄別過濾;二是輸出使命,電影的政治力量的關鍵在于本國文化的輸出,當然所有的文化都不是完全等同的,異質文化間遭遇之時,無法避免產(chǎn)生誤讀,甚至是矛盾和沖突,因此,如何異中求同,怎樣異中存異,電影承擔了化解沖突和融合交流的任務。盡管在文化輸出的過程中,其他的力量也在發(fā)揮各自應有之力,比如小說跨國界的輸出,但是純語言文字的表達方式,在經(jīng)歷翻譯的二次創(chuàng)作后,原作與譯作的間隙是難以彌合,小說文字間隱含的信息解讀需要具備一定文字素養(yǎng)的受眾,閱讀小說的受眾遠遠低于觀影的人群。而電影傳遞信息的容量和力度都更具優(yōu)勢,它可以減少文字語言傳遞信息中的阻力,并能以較為快捷和廉價的傳播方式,抵達國外大量的觀眾面前。
電影作為社會教育,其社會力量內涵包羅萬象,而教育功能是最重要的部分,這體現(xiàn)在電影能夠傳達出正確的價值觀等正面力量,并能為觀眾接受。觀眾的接受基于普遍的人性,阿蘭·巴迪 歐 稱 之 為“ 一 般 人 性 ”(humanité générique)”①。比如,美國人、中國人、英國人、埃及人都能夠超越彼此之間的差異,喜歡卓別林的電影,并從中收獲人類共有的歡喜與辛酸;或者,從積極方面看待超級英雄影片的效果,此類電影展示了人類團結互助的情境,激發(fā)出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正義感。電影作為一門大眾藝術,其受眾數(shù)量的龐大,使得其一旦發(fā)揮出教育的效果時,電影的社會力量則能夠勝任社會成員的教育。
電影的藝術力量較政治、社會力量而言,更具深入性、牢固性和持久性,藝術力量是三重力量的核心②。劉恒認為,藝術的力量來自于藝術經(jīng)典。經(jīng)典能超越時空,抖落曾經(jīng)附著于其上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的屬性,保持藝術純真的內涵本質,給予后世藝術滋養(yǎng)。換種說法,某藝術因其內在的深刻性,連接人類共通的感受。當人類的共通感在藝術經(jīng)典中串聯(lián)時,藝術的力量得以顯現(xiàn),它觸發(fā)人的感動,通過情感與理性的進一步交融,人意識到人生的意義,最終,電影的藝術力量孕育出涵化的作用 。
電影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藝術力量,三者在各自的領域發(fā)揮作用,政治力量在國與國的競爭中,體現(xiàn)出防守與輸出的態(tài)勢;社會力量在面對觀眾時,施展出教育宣傳的力量;藝術力量則抵擋時空的侵蝕,保存了經(jīng)典的價值,展示出化育人心的作用。
找出不同領域、概念和事物之間的差異,其實是初步的,正如電影的三個力量,它們各自的屬性相異,但是如何求同存異,發(fā)掘差異中的共同之處,則需要哲學思維的介入。劉恒指出,三個力量的共性都涉及“形而上”“形而中”以及“形而下”的問題。形而上可以用中國道家的“道”解釋,理解為主旨或理念;形而中是共性中的核心,是指電影人的品質和狀態(tài);形而下則可以理解為 “器”,即運用具體的工具和創(chuàng)作手法。本質上,劉恒的分類范式反映出中國傳統(tǒng)的天人合一的哲學觀。他將形而上中下分別對應天地人三才。不同于西方的主客對立,中國的三才觀念是三者的緊密結合。劉恒在論述形而上中下時,并非涇渭分明、彼此毫無指涉,而是采用了十五組反義詞,清晰梳理出電影中具體的形而上中下,體現(xiàn)出相互鏈接的圓融平衡狀態(tài)。
二、電影本體論:形而上
劉恒對電影形而上的看法,本質上是他的電影本體論觀點,他認為電影的本質是“道”的體現(xiàn),“道”的內容具體表現(xiàn)為生死、愛恨、善惡、禍福和新舊等主旨或理念。
首先,劉恒對藝術的起源做了論述,進一步講解藝術的資源和動力。人類所有的生產(chǎn)生活活動都圍繞著生與死,藝術作品的主旨總是離不開生死的主題,其中,死亡是永恒的創(chuàng)作來源。劉恒從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威爾第的生命遭遇和藝術創(chuàng)作中,發(fā)掘出死亡對于藝術的啟發(fā)和推動,他回溯藝術與死亡的關聯(lián),認為藝術起源于巫術,因為人對死去親人的回憶,以及對生的渴求,使得原始巫術產(chǎn)生出將人留下來的替代物,比如在死者臉上倒模,制作出面具,并在面具上做一定的描繪①。面具的產(chǎn)生相當于死者的身體在場,這種轉換方式代表了早期藝術起源之際,人以圖像(面具)充當身體,以面具的在場象征生的在場。以至于出現(xiàn)巖畫、繪畫、雕塑等,今天視為藝術的產(chǎn)物,其背后都根植有深刻的生死觀念,以至于19世紀出現(xiàn)攝影術之后,照片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專攻人像攝影,背后透露出人希望通過影像將生的另一種可能留在世界。正是在梳理藝術的起源問題上,劉恒發(fā)掘出,藝術的產(chǎn)生填補了人類 “向死而生”的愿望。藝術永恒的主題是生與死,本質上,藝術的永恒在于人本身,人對生的渴求是藝術不絕的源泉和永恒的動力支撐。
他提出,由于競爭的緣故,人產(chǎn)生了愛恨。愛恨的觸發(fā)點,都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之爭,并產(chǎn)生出恨意和恨的行為。他關于愛與恨的解讀是從社會屬性的角度出發(fā),比如,他列舉《小丑》《寄生蟲》等電影,指出影片中的主人公的恨,來自于社會競爭的不公與打擊。但是,這一觀點有待補充。筆者認為愛并不僅僅來自于競爭,比如父母與子女之愛,則更多地體現(xiàn)出了人類無私的情感范疇。例如《鋼的琴》里的主人公,面對下崗和離婚的雙重打擊,想盡各種辦法滿足女兒擁有鋼琴的愿望,最終,鋼琴真的以“鋼的琴”的方式出現(xiàn)。外國影片《美麗人生》也是講述了父親對孩子的疼愛,為了不讓兒子受到戰(zhàn)爭的摧殘,父親“欺騙”孩子說納粹集中營是一個贏取禮物的游戲場所,用各種各樣的方式營造出童話的氛圍,最后,父親慘死在納粹槍口下。這兩部影片的主人公,本可把投入在孩子們身上的一切,轉為自己生命保存的可能,但他們都選擇了前者,這都是出自于對子女無私的愛,才會促使他們迎難而上,甘于奉獻自己的所有。
為什么劉恒沒有提及愛的無私之處?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或許可以解讀劉恒觀點的實質。劉恒的創(chuàng)作生涯起步于文學寫作,其小說《狗日的糧食》《伏羲伏羲》等作品中,都展示了小人物的生存狀態(tài)和悲觀主義的筆調,而這種創(chuàng)作傾向,也體現(xiàn)在他轉向電影劇本的創(chuàng)作領域,依然保留著對普通人現(xiàn)實處境的直接揭露,類似于魯迅對人性的冷峻的態(tài)度和一針見血的書寫。劉恒直言“:我讀了他幾乎所有作品,包括日記和書信。那種癡迷的閱讀剛好發(fā)生在我的青少年時期,印象太深了。我對他的崇敬之深,幾乎可以說是沒有理智可言。他對我的寫作產(chǎn)生了非常大的影響。”②劉恒的創(chuàng)作傾向,決定了他對人本身保有冷靜的思考,這是闡釋其電影創(chuàng)作美學不可忽視的方面。
除此之外,還可以有另一種解讀,劉恒將人性的無私放在善與惡的抉擇中。在他看來,決定人類活動取向的是競爭,正因為競爭之殘酷,因此,造成了兩種分化。一種是“惡”的想法在競爭中凸顯出來,諸如暴力電影;另一種則是“善”的觀念的突圍、競爭而促發(fā)人性的正面性、光輝點和崇高處,如劉恒的《秋菊打官司》《漂亮媽媽》《張思德》《云水謠》。
正是因為對人的聚焦,對人的命運與個體的遭遇的關注,劉恒提出第四組反義詞——禍福。在他看來,禍與福的轉化都是人生的常態(tài),因而人的命運具有不可預測性,所能擁有的幸福又總是相對的。面對禍福的劇烈變化,人總是會心生恐懼感,現(xiàn)代人的焦慮與日俱增,而藝術將這種不可預知的經(jīng)過與未來剖析展示出來,創(chuàng)造出撫慰人心的精神價值。
最后,劉恒的電影本體論落腳于對新舊的思考。他既不贊同“舊”阻礙“新”,也不贊成“新”打敗“舊”,而更傾向于新舊之間的平衡。其實,劉恒僅將這一組反義詞點到即止,但是從他的態(tài)度可以推知,電影的主旨與理念并不是固守的存在,也不是一味地逐新,人類藝術的主旨具有永恒性,如生死、愛恨、善惡、禍福,都是歷史中人類需要面臨的主題,但是歷史的發(fā)展,不僅有共性,也有不同時代所產(chǎn)生的差異性,即新的主旨或理念、新的主題的出現(xiàn),而這個“新”正是某一時代特有的產(chǎn)物。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他所提出的新舊,正好概括了其電影本體論,電影的本質是“道”,“道”的內容是人類共有的、永恒的生死、愛恨、善惡和新舊的主旨,而新舊既屬于電影本質的不變性,也涉及了電影本質不變之中的變化,穩(wěn)定之中的動態(tài)化。
三、電影創(chuàng)作論:形而中和形而下
圍繞電影本體論的闡述范式,劉恒還提及了電影的“形而中”和“形而下”的十組反義詞,本文將后兩者合稱為劉恒的電影創(chuàng)作論,分別對如何創(chuàng)作電影做了宏觀分析和微觀把握。
劉恒認為電影力量的“形而中”,涉及人的 “心”①,處于形而上中下三者中最核心的位置。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說,人“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在天地人三才中,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為人的存在和人語言的創(chuàng)造(在這里可以狹義地理解為藝術),才能連接起天地萬物。電影是人的語言在現(xiàn)當代的創(chuàng)造物,劉恒對電影創(chuàng)作的五組反義詞,構成了其對電影創(chuàng)作的理解,本文將之稱為劉恒的電影創(chuàng)作論的宏觀內容。
劉恒提煉出,悲與喜是電影的表達形式,從外延上看,電影分悲劇與喜劇;從內涵而論,電影展示人情緒中的悲傷與喜悅。他認為,最好的藝術表達形式應為悲與喜的融合,比如電影《小丑》中的主人公,總是以悲喜混雜的情緒流露,給觀眾產(chǎn)生了巨大的沖擊力。電影的創(chuàng)作表達應努力挖掘出多元復合的人類情緒,單一的悲劇或單一的喜劇并不是人生的常態(tài),藝術來源于生活,理應表達出人類情感的復雜狀態(tài)。
對于電影表達的態(tài)度,劉恒總結為“信”和 “疑”,前者是一種正向的信念,通過創(chuàng)作,將電影中的正能量傳遞給觀眾,比如國慶獻禮影片對主旋律的宣傳頌揚。后者“疑”則是一種批判的態(tài)度,電影的創(chuàng)作需要對準現(xiàn)實中的問題和陰影,并保持正向引導的姿態(tài),不是以殘酷回饋現(xiàn)實的殘酷,藝術也應高于生活,指出殘酷中細微的溫情。
雅與俗的問題,一直都是藝術領域相互博弈的風格范疇,電影的創(chuàng)作也不例外。劉恒指出,電影在上世紀早期至中葉,屬于“雅”的領域,備受精英推崇,隨著資本的介入,電影的商業(yè)化、大眾化特征壓倒了對“雅”的追求,因此,現(xiàn)在的電影創(chuàng)作,面臨是否需要“雅”的創(chuàng)作,以及這種創(chuàng)作何以可能的問題。對此,劉恒持樂觀的態(tài)度,他認為在商業(yè)化的處境下,優(yōu)秀的電影人依然可以創(chuàng)作出既叫好又叫座的影片。這方面成功的范例有《集結號》。該影片由劉恒擔任編劇,故事放棄傳統(tǒng)的英雄主義敘事,轉為記錄普通士兵的故事,挖掘出人性中樸素而光輝的一面,該片收獲大量優(yōu)質好評,并獲得近2.6億的票房,稱得上既叫座又叫好的國產(chǎn)影片代表。王一川認為,該片成功融合了電影的主導價值、藝術價值和觀賞價值,實現(xiàn)政府、專家及公眾的三重好評,具有深遠的轉型。② 至于“俗”的問題,大部分的電影都對此有所涉獵,這取決于電影本身是一門大眾藝術,不是少數(shù)精英的專屬,電影的受眾群體決定了其本身,不可能脫離“俗”,不可能不涉及大眾的日常本身。劉恒指出,電影的創(chuàng)作必須落到地面上,不能脫離底層,必須關注底層小人物的情感與遭遇,有時甚至需親身經(jīng)歷生活的嚴苛。縱觀劉恒的創(chuàng)作生涯,其小說、影視劇本等的創(chuàng)作與改編,都聚焦小人物的生存和命運,以平等的視角看待一切,具有鮮明的平民主義情懷。正是精妙地運用“俗”這個風格范疇,劉恒的創(chuàng)作踏出一條不媚俗、不庸俗和不惡俗的“俗”的藝術創(chuàng)作道路。
關于電影的虛實問題討論,也是他對語言的認識,以及對電影創(chuàng)作構思的思考。一直以來,對電影的討論中,有一種觀點認為電影是現(xiàn)實的再現(xiàn),因此,電影反映現(xiàn)實,以及從一定程度上講,電影是現(xiàn)實的記錄。但是,劉恒并不贊成這種觀點,他認為同一內容用不同語言表達,所呈現(xiàn)的效果是不同的,這是因為作為語言表達的主體——人,其感性與理性是不穩(wěn)定的存在,總是處于變動之中,這兩者共同影響語言的表達使用,因此,使用不同的語言表達相同的內容,會產(chǎn)生具有差異性的結果。劉恒的藝術語言觀體現(xiàn)出其后現(xiàn)代語言哲學的傾向,即語言不是真實的,語言本身具有不確定性,是游移多元的,不是傳統(tǒng)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對語言的懷疑,打開了劉恒對電影創(chuàng)作構思的討論,正因為語言本身不可信,藝術的創(chuàng)作反而獲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合法權,作者運用電影語言時,可以擺脫邏各斯的完全控制,能夠進行探索、觸摸和猜想,打開日常生活中緊閉的邊界,創(chuàng)作的思維活動把想象的虛構與外在世界相協(xié)調,甚至豐富的想象活動超越現(xiàn)實世界的界域。就像《流浪地球》,構造出未來地球的命運和生活圖景,使得人對自身存在有所深思,并延伸至未來之境,鏈接起當下、現(xiàn)實和將來,而目的是回到當下的處境中。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循環(huán)過程。電影的創(chuàng)作構思是超越時空限度,指向未來的某一時空,但是創(chuàng)作的構思同時反指涉當下的境況,而這一切的實現(xiàn)都依賴于創(chuàng)作構思的想象與虛構的運用,于是,虛構在電影的美學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對電影創(chuàng)作的討論中,劉恒流露出對電影商業(yè)屬性的關注。一方面,他指出電影主題表達得越深刻,影片所具有的藝術價值也就越高;另一方面,他沒有回避電影深刻化、精英化會導致的問題,因此,他明確表明電影本身具有商品的特征,制作電影要慎重考慮藝術深刻與商業(yè)普及之間的平衡。為此,他提出“深”與“淺”的討論。電影作為不純的藝術,本身就離不開錢這個話題,上世紀早期,本雅明就考慮到電影并不是單一的成就,決定電影演員成就的并非演員自身,而是來自于燈光、資金等多個因素的成就集合,這就意味著電影的誕生包含著價格不菲的投入,它必須面向廣大的觀眾群體,觀眾成為支付投入的重要群體。①到 21 世紀初,巴迪歐也認為,電影是一種絕對不純的藝術,它產(chǎn)生于獨特的物質組合,需要技術資源、地點、材料布景,還需要文本、身體、聲音等等,還需要不菲的資金支持。②本雅明和巴迪歐都認同電影并不是純粹的藝術形式,在電影身上,展示出藝術與商業(yè)之間最大的對抗共生性。電影自產(chǎn)生之初,就與商業(yè)息息相關,與大眾的接受密不可分。在最大的程度和最多的數(shù)量上而言,電影不可能是孤芳自賞,盡管我們并不否認有這樣的電影存在,電影作為一部作品和商品,其完成的結果達成依賴大眾的參與。這種參與來自兩方面,一是電影的誕生依賴資本的投資,而投資意向依賴潛在的大眾購買群體;二是電影藝術與商業(yè)屬性的協(xié)調,來自于大眾的評價與贊譽,這里大眾包含精英群體。劉恒關于電影創(chuàng)作的深淺問題,折射出藝術的取向與商業(yè)策略平衡,對于創(chuàng)作者來說,這種平衡是其如何運用好“電影生存和發(fā)展的社會、金融與美學相交融的修辭術”。③
以上五組反義詞構成了劉恒的電影觀中的 “形而中”部分,“形而中”是其創(chuàng)作論的宏觀部分,涉及了電影的表達形式、電影表達的態(tài)度、風格范疇、語言觀和創(chuàng)作構思,以及電影藝術性與商業(yè)性的平衡等五個問題。在此宏觀創(chuàng)作的視野基礎上,劉恒進一步探討了電影的“形而下”部分,主要談論電影的創(chuàng)作技巧,分別是信息傳遞的先后順序,創(chuàng)作時如何處理時間的問題;其次,整體與局部的主次安排,怎樣在創(chuàng)作空間上把握全局的主導性;第三,站在靜態(tài)的角度,如何對創(chuàng)作內容進行加減;第四,從動態(tài)維度入手,電影鏡頭通過 “急”與“緩”,制造出蒙太奇時間以及“靜態(tài)拉伸的時間”①,成功的電影總是能呈現(xiàn)出這兩種影像時間;最后,技術運用和電影敘事的強弱關系,技術的迭代更新,制造出令人驚顫的效果。但是,劉恒提醒,唯技術論并非是電影發(fā)展的最佳選擇,創(chuàng)作不能迷失在技術的道路上,還應考慮電影的敘事語言和講述方式,偉大的電影作品總是能用樸素的方式打動人心,能打動人心的是人的生死、愛恨、善惡、禍福和新舊。在這意義上講,電影創(chuàng)作的“急”與“緩”,從“形而下”的技術層面,回歸到 “形而上”的哲學思考,劉恒的電影創(chuàng)作論和本體論之間不是單一的分隔論述,而由其能在的圓融之處。
四、電影創(chuàng)作者的智慧與能力
從電影的三重力量,到電影的形而上中下,劉恒對電影的討論包含了電影的效果論、本體論和創(chuàng)作論,這三論都共同期待于電影創(chuàng)作者的綜合職業(yè)表現(xiàn)。因此,劉恒在整篇演講稿中,均提及了電影創(chuàng)作者應具備的智慧與能力。他指出,創(chuàng)作者是“影視視覺藝術最終的且是直接的書寫者”②。一部影片的質量和影響力,與電影創(chuàng)作者的職業(yè)素養(yǎng)和能力緊密相關。
首先,創(chuàng)作者需積累職業(yè)才能,培養(yǎng)自律精神。他特別強調創(chuàng)作者的知識積累、社會觀察和經(jīng)歷體驗。作為創(chuàng)作者,不僅僅需要掌握書本知識,還要做充足的社會調查,關注人的心理的細微變化,身體力行進入相關領域體驗人生。他列舉吳京的經(jīng)歷做說明,吳京早年做替身演員時,在片場勤學多練,學到了諸多本領技巧,為其成為導演打下牢固的基礎;其實,劉恒本人也是電影編劇的行業(yè)典范,為完成《集結號》的編劇任務,他研究了上百部有關解放戰(zhàn)爭的書籍,寫有3萬字的主題分析和6萬字的腳本,結合曾經(jīng)當兵的經(jīng)歷,在寫作時播放前蘇聯(lián)的音樂,營造寫作的氛圍,寫到動情之處,淚流不止。④劉恒還提到張藝謀謝絕了自己的演出贈票,專心投入劇本的挑選工作的自律。古今中外,偉大的作品背后幾乎都有勤于創(chuàng)作、嚴于律己的創(chuàng)作者。如果說創(chuàng)作者分天才與地材,顯然劉恒更為看重持之以恒地積累創(chuàng)作才能的后者。
第二,創(chuàng)作者需具備適應環(huán)境的能力。劉恒并不反對電影中的商業(yè)元素,在他看來,電影不是純粹的藝術,包含了藝術與非藝術的成分,非藝術涉及資金、場地、設備、票房回報等。電影的創(chuàng)作不能脫離電影本身的生存以及與電影相關的一系列的人的生存問題,創(chuàng)作者必須考慮電影整體的生存,以適應“最廣大的公眾群以及相應的社會心理、社會體制、文化藝術機制、意識形態(tài)調適等遠為寬闊的層面”④。
在劉恒看來,上述能力最終落腳于創(chuàng)作者發(fā)揮出的藝術平衡智慧。劉恒提到“智慧”與“愚蠢” 一組反義詞來說明“平衡”的藝術能力,在本體論中,選擇任何某個或某些理念(如善惡)進行表現(xiàn),以及影片中某個或某些理念占比,創(chuàng)作論的五個方面(電影的表達形式、電影表達的態(tài)度、風格范疇、語言觀和創(chuàng)作構思,以及電影藝術性與商業(yè)性的平衡),這些都涉及平衡的智慧。偉大的作品總是藝術平衡后的產(chǎn)物,而拙劣之作往往失衡掉進創(chuàng)作的陷阱。
綜上所述,在后現(xiàn)代的文化氛圍中,去中心和去本質化已經(jīng)成為主流,精英藝術與大眾藝術的裂痕持續(xù)裂變,劉恒仍能秉持清晰的電影本體論思路,發(fā)掘電影的政治、社會和藝術等多重力量,兼顧電影的藝術性和商業(yè)性,提升了電影,尤其是商業(yè)電影、大眾電影的藝術地位。他的電影創(chuàng)作論,為青年導演提供了創(chuàng)作的思路和綜括的范式,其關于電影人應具有的智慧和能力的看法,為電影創(chuàng)作的實際落地提出了可行的方法。隨著電影成為當代的主流文化消費藝術之一,電影本身的不純性,怎樣的電影可以深入人心,怎樣的電影能夠躋身經(jīng)典藝術的殿堂等諸多問題,通過劉恒關于電影的本體論、創(chuàng)作論和電影人論可以提供一種清晰辯證的思路,其對青年電影創(chuàng)作者給予深厚的期望,希冀通過他們的創(chuàng)作實踐,誕生出經(jīng)典的電影作品,發(fā)揮出電影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藝術力量,開拓人類精神文化領域的創(chuàng)造邊界,以電影的語言形式,守護人心靈世界的本質部分,至少,還能憑借電影“遠離失望”。①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