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雖然《武訓傳》《關連長》為迎合新意識形態做出了各種努力,《早春二月》《林家鋪子》真實地、歷史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逆風千里》《兵臨城下》取材于真實的歷史故事并經由多層領導審查通過,但是在“十七年”時期都被全國批判。歷次電影批判都要求創作者的創作思想和歷史敘事方法發生全新的變化,以適應電影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集中體現人民最關心的主題:人民為爭取解放而斗爭的主題,以及在革命烈火中廣泛地改造人的主題。
關鍵詞:歷史描述;歷史闡釋;歷史人物評價;反歷史主義;歷史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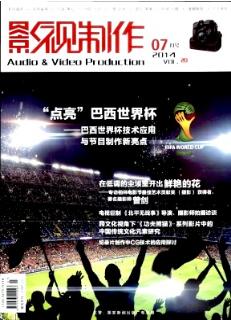
《影視制作》(月刊)創刊于1994年,是由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主管,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廣播電視規劃院主辦、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科技委電視中心專業委員會協辦的國家級影視節目制作專業期刊。
歷史題材在中國電影藝術發展史上始終是一個重要且特殊的存在,在“十七年”(1949—1966)時期更是得到全新塑造和組裝。歷史題材作為電影創作中的一種文化資源,在什么時期可以利用,在什么時期應該有選擇地利用,以及在什么時期被完全摒棄,亦即它的揚與棄、利與弊,都取決于它能為現實/政治帶來多少公共利益。如何對待和處理歷史、歷史人物和歷史生活,成為新中國電影歷史敘事的核心命題。不僅革命戰爭題材和革命歷史題材電影關涉電影的歷史敘事,那些表現歷史生活的電影也面臨著如何藝術地演繹普遍的歷史發展規律的問題。
一、《武訓傳》《關連長》批判與原國統區文藝隊伍的思想改造 歷史人物作為一種可被利用的資源,他對闡釋者自身具有怎樣的現實價值和意義常常主導著對于他的解釋原則。選擇怎樣的歷史人物納入現實政治完全由現實政治需要來決定,而且歷史人物的實在是由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出于道統觀念對武訓幾乎如出一轍地將其尊為“圣人”。在中國文藝泛政治化日益明顯的趨勢下,早年那些不被共和國初期主流意識形態認可的評價,對電影《武訓傳》(1950)的主題與其理論正當性造成了闡釋邏輯上的分裂和脫節。過去時代統治者的視域,如何可能被現實政治需要來形成自為的現在視域?電影《武訓傳》的拍攝經歷新舊時代,先后緣起于陶行知的大力支持,以及原本持歷史人物過時論的郭沫若的題詞支持,周恩來的指導意見則為影片對武訓的新時代定位及其歷史局限性評論提供了重要支撐。他們的評價是《武訓傳》“歌頌加批判”敘事框架的重要理論來源。盡管如此,添加農民起義等意識形態話語且多番修改過的《武訓傳》事與愿違地向構成物轉化,而這一構成物就是武訓對舊時代統治階級投降的不抵抗主義。宣揚教育救國、階級調和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走向了投降主義。歌頌一個與農民起義和階級斗爭相向而行的、相違和的歷史人物,與毛澤東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理論產生抵牾,當然也就偏離了國家意識形態和權威敘述的軌道。
1951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指出,《武訓傳》歪曲了農民革命斗爭及其歷史傳統,“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說明了“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1]這篇社論主要是以國家意識形態批判性話語來徹底地澄清影片及其他與武訓相關的論文、著作中存在的“思想上的混亂”問題,以求根本性地解決闡釋歷史的理論依據和方法資源問題,進而實現整合歷史闡釋的意圖。發動這場卓有威效的政治批判,是為了縮小或肅清傳播資產階級思想“毒素”的電影的市場、勢力和影響,達到確立和強化新政權合法性、權威性詮釋的最終目的。它解決的不僅是文藝工作者該闡釋什么樣的歷史,而且規定了應該怎樣闡釋歷史,以及評價歷史人物的問題。批判性話語對歷史題材電影創作和批評中缺乏正確的政治方向規范、理論資源使用,以及其中包含的知識—權力關系等問題,都以非此即彼的、激進主義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給予厘清。
如何在銀幕上正確塑造英雄形象,是橫亙在新中國初期原國統區文藝工作者面前的難題。因為不熟悉工農兵的生活,需要專門去調查和體驗才可以創作。《關連長》的導演兼主演石揮原本充滿創作熱情和激情,他曾對記者說,“拍完了這一部戲,他等于從軍了三年回來,因為他自從該片開拍前在部隊中體驗生活直到拍完《關連長》片后,對與他們的生活和勇敢作戰的經驗學習得非常豐富。”[2]上海解放時,關連長為了保護孤兒院的數百名孤兒,不直接向敵軍指揮所展開炮擊,改用白刃戰,最終消滅了敵人,關連長也光榮犧牲了。然而,保全兒童們生命的《關連長》(1951)卻被批判為“以庸俗的小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歪曲了我們人民解放軍的革命人道主義”,并且“嚴重的歪曲和誤解了人民解放軍的優秀本質和英雄形象”。
批判者主要集中于批評《關連長》歪曲了人民軍隊的形象。“影片作者以小資產階級的觀點、方法去觀察生活,去理解士兵,去創造角色,迎合小市民低級趣味,偏愛地攝取了部隊生活中極個別的、非本質的、非人民軍隊氣質的落后現象,盡情地加以渲染;而忽略了普遍的、全體的、本質的向上急劇進展的積極事物,這樣就必然發生了上述的一些現象。這樣就使得原來是最可愛的人物——我們的戰士被丑化了。”[4]1953年6月,陳毅也曾對《關連長》提出批評:“電影《關連長》,片中所塑造的形象就很不像樣子。關連長開口罵人,軍衣扣子不扣,蹲在板凳上,叼著旱煙袋,完全一副落后農民的形象。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我們的指揮員、戰斗員是有高度軍事素養和文化素養的,所以才能夠武裝奪取了政權。文藝工作者應當在文藝作品中歌頌他們為革命事業英勇斗爭和壯烈犧牲的那種無私無畏的精神面貌,這才是正確的創作思想和創作態度。文藝的美學,就是要表現沙粒中閃光的一點,從紅軍時代起,我軍就具有正規化的特征。所以在電影上我就不贊成把中國人民解放軍寫得不扣風紀扣,歪戴帽,斜背槍,一副吊兒浪當的模樣。游擊習氣在部隊創業初期是存在過的,但不是普遍的現象。藝術主要的任務是表現生活中的真善美,而不是生活中的假丑惡。”[5]
導演孫瑜、石揮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藝思想不甚了解并表現出對電影服務對象根本性轉變的不適應。再加上私營電影業與生俱來的商業性趨向,都與不斷闡釋和正在規范中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顯得格格不入甚至相撞。《武訓傳》《關連長》等作為原國統區文藝工作者創作、私營電影公司生產的體制外作品,在當時的意識形態范疇內兼具兩者之害是顯而易見的。盡管昆侖影業股份有限公司、文華影片公司生產的這兩部私營電影能夠讓人明顯感受到其為迎合新意識形態所做的各種努力,但因為未達到后者所需要的政治宣傳和思想教育作用,它們的創作積極性非但未得到正向度的鼓勵和引導,反而招致全國范圍內粗暴的政治批判乃至上海文藝界自虐式的上綱上線的自我批評。
這些有具體針對對象的批判,幫助文化藝術界按照國家意識形態的標準樹立了歷史唯物主義觀,確立了歷史描述或歷史闡釋的指導思想:對待革命的人民(工農兵)應該要視為新事物、新人物、新思想來歌頌;對待知識分子出身的歷史進步人物,要視為人民的同盟者來表現他們的民主性、革命性,同時也要寫出他們的歷史局限性及其思想改造;對待來自封建地主、買辦、官僚資本家出身的和外國侵略者等敵對階級要給予無情的暴露和批判。這些成為后來很長一段時期內衡量電影歷史敘事的重要標準。
雖然這些轟轟烈烈的政治批判運動達到了發動者要求的重構知識分子政治認同和整合文藝作品闡釋歷史的目的,但仍然夸大地估計了資產階級的力量及其政治思想對文化藝術界和黨的負面影響,過火地采取了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方式,傷害了知識分子對新政權的情感。這對那些渴望獲得正面引導和幫助來實現思想轉變和藝術提高的原國統區進步文藝工作者來說,是極為不公正的。其實,他們在新中國建立初期是懷有真誠的改造愿望的,也希望積極配合愛國主義宣傳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高潮,只是他們客觀上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受過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教育的深刻影響,主觀愿望與客觀條件還有一定的差距,一時還達不到國家意識形態的標準。因而,急躁地發動這種政治批判運動,挫敗了他們追求進步的自覺性,不利于整個文藝事業的健康和平穩地發展。
二、《早春二月》《林家鋪子》批判與人道主義、人性論 表現知識分子苦悶與彷徨的《早春二月》(1963)改編自柔石的小說《二月》,描寫民生凋敝的《林家鋪子》(1959)改編自茅盾的同名小說。兩部影片是根據優秀的現代文學名著改編的,分別以知識分子、工商業者為主角,講述了不同人物在時代洪流中漂泊流離的命運和身不由己的選擇,先后在1964年夏、1965年春夏之交開始遭到批判。批判話語主要集中于帶有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人性論的錯誤。批判者認為,對于這兩部影片的批判,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種意識形態、兩種文藝觀點的斗爭在文藝領域內的反映。
1962年8月24日,夏衍和陳荒煤來到北京電影制片廠討論《二月》劇本時建議:把大革命時代的背景表現出來,就能把人物的精神面貌寫得比較準確;只有忠實于當時的時代,人物才可以比原作寫得高些;劇本的對話太露,要含蓄一些;陶嵐的出走比蕭澗秋更大膽,結尾對她要有交代。[6]1962年11月25日,謝鐵驪把分鏡頭劇本送給夏衍。幾天后,夏衍便把分鏡頭劇本退回,并附上一封信。影片分鏡頭本只有474個鏡頭,夏衍精心批改、批注的大約有160多個鏡頭。提出的意見大致如下:強調當時的時代氣氛;注重含蓄;強調細節的真實;建議片名改為《早春二月》。[6]1963年8月23日,文化部正式審查,導演按照夏衍和陳荒煤的意見又補拍了一些鏡頭,并做了細致的修剪。1963年11月1日,夏衍和陳荒煤陪同周揚、沈雁冰、張光年等來到了北京電影制片廠,一起審看了《早春二月》的完成樣片。周揚同志聽到大家肯定和贊揚的發言后,臉色卻不大好看。他一開口就向大家表示:“不喜歡這部影片。”周揚說,改編一點“五四”以來的作品,他也不反對,“但是要挑選得適當,而且應有所批判”。柔石“那時是受了托爾斯泰的影響”,現在有些情節原樣出現,“看了就很不舒服”。周揚還說,蕭澗秋要和文嫂結婚,這“是一種武訓精神”,這種精神不值得表揚。“這是一種妥耶夫斯基的自我犧牲、自我摧殘的悲劇,今天的青年人不能理解”。柔石的“這個作品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再版,而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是應該批判的”。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