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中國(guó)文學(xué)史發(fā)軔時(shí)期( 1900—1910) ,一批以近代大學(xué)堂、中學(xué)堂、師范學(xué)堂“中國(guó)文學(xué)”科教科書(shū)身份出現(xiàn)的中國(guó)文學(xué)史著作,其內(nèi)容除傳統(tǒng)文章流別外,還包括傳統(tǒng)小學(xué)、文法、修辭、文章作法等,與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學(xué)史模式迥然不同。這種早期文學(xué)史“另類”模式的形成是晚清教育改革、近代學(xué)術(shù)體系變遷、中西交流背景下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復(fù)歸的精神訴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作為“西學(xué)東漸”的產(chǎn)物,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編撰不免會(huì)受到西方、日本外來(lái)資源的影響。這其中,來(lái)自日本“漢文典”的重大影響往往被學(xué)界所忽視。以保存“舊學(xué)”為出發(fā)點(diǎn),以“普及漢學(xué)”為教育旨?xì)w,以中國(guó)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為主導(dǎo),套用西洋語(yǔ)法著作模式外殼的日本“漢文典”,最早實(shí)現(xiàn)了中西學(xué)術(shù)的有效整合,并與晚清教育改革“中體西用”的價(jià)值觀念相契合。日本“漢文典”被迅速引介入華后,不僅對(duì)新式國(guó)文教育下的文法教學(xué)產(chǎn)生重要影響,也為文法教科書(shū)及中國(guó)文學(xué)史編撰提供了借鑒。梳理日本“漢文典”內(nèi)容、體例模式及其實(shí)踐路徑對(duì)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編撰產(chǎn)生的影響,能夠明確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如何接受與吸收以“漢文典”為代表的外來(lái)資源,以及中西交流背景下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體系如何嘗試完成近代轉(zhuǎn)型。
關(guān)鍵詞: 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 “另類”模式; 漢文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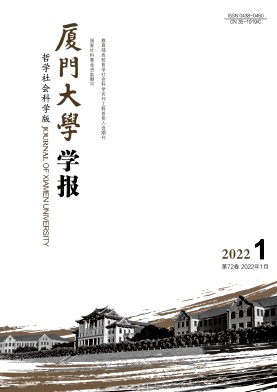
李無(wú)未; 張品格 廈門(mén)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22-01-27
一、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另類”模式構(gòu)成
( 一) 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另類”模式
晚清以來(lái),隨著西學(xué)東漸的大潮,加之新式國(guó)文教育的推廣,我國(guó)學(xué)者自行編撰的“文學(xué)史”登上歷史舞臺(tái),以林傳甲《中國(guó)文學(xué)史》( 1904) 為嚆矢。一般認(rèn)為,20 世紀(jì)的前十年( 1900—1910) 為中國(guó)文學(xué)史“發(fā)軔期”。①這一時(shí)期我國(guó)學(xué)者編撰的中國(guó)文學(xué)史著作無(wú)論是在體例模式、結(jié)構(gòu)抑或內(nèi)容方面,都有別于當(dāng)時(shí)西洋、日本流行的文學(xué)史著述。以林傳甲《中國(guó)文學(xué)史》( 1904) 、劉師培《中國(guó)文學(xué)教科書(shū)》( 1906) 、黃人《中國(guó)文學(xué)史》( 1907) 、來(lái)裕恂《中國(guó)文學(xué)史稿》( 1909) 為代表。舉凡傳統(tǒng)小學(xué)、文法②、修辭、文章學(xué)等非文學(xué)史內(nèi)容幾乎都包含其中,與其說(shuō)是文學(xué)史,更像是融合了中國(guó)固有之學(xué)的學(xué)術(shù)史。這類文學(xué)史著作還有一個(gè)顯著的身份,便是近代新式國(guó)文課堂“中國(guó)文學(xué)”科教科書(shū)。因此,與后期以西方文藝?yán)碚摓榛A(chǔ)的“新”文學(xué)史研究著述相比,最早以“教科書(shū)” 身份出現(xiàn)的中國(guó)文學(xué)史著作兼及學(xué)堂科目、著述體例與知識(shí)系統(tǒng)①,在體例模式及內(nèi)容構(gòu)成方面有一定區(qū)別。
目前學(xué)界一般認(rèn)為,我國(guó)最早的文學(xué)史著作出自林傳甲( 1877—1922 ) 的《中國(guó)文學(xué)史》 ( 1904) 。這原是京師大學(xué)堂“優(yōu)級(jí)師范科”國(guó)文課程授課講義。該書(shū)共十六篇,內(nèi)容包括小學(xué)、文法、詞章、經(jīng)學(xué)、諸子文體及歷代文章流別,其中關(guān)于文字、音韻、訓(xùn)詁等傳統(tǒng)小學(xué)的論述占了很大篇幅,成為引人注目的文學(xué)史內(nèi)容之一。1907 年,黃人( 1866—1913) 為東吳大學(xué)②國(guó)文課編撰國(guó)文教材《中國(guó)文學(xué)史》,較之林傳甲書(shū),其視野更加開(kāi)闊。作者不僅接受了西方美學(xué)思想、文藝?yán)碚摚€將前人鄙薄的神話、小說(shuō)、戲曲、雜文等通俗文學(xué)納入文學(xué)史體系之中,但仍然包含文字、韻學(xué)等小學(xué)、經(jīng)學(xué)內(nèi)容。這一時(shí)期,作為海寧中學(xué)堂國(guó)文課講義的來(lái)裕恂( 1873—1962) 《中國(guó)文學(xué)史稿》( 1909) 也取 “學(xué)術(shù)史”模式,但小學(xué)的內(nèi)容明顯減少。這并不是來(lái)裕恂不重視,而是將小學(xué)內(nèi)容轉(zhuǎn)移到同為國(guó)文教材的《漢文典》( 1906) 中。這部《漢文典》是來(lái)裕恂于 1904 年赴日留學(xué)后,參照日本文典引進(jìn)西方最新“語(yǔ)法”內(nèi)容撰寫(xiě)的一部集文字、文法、文章、文學(xué)于一體之作。從內(nèi)容上看,《中國(guó)文學(xué)史稿》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抄錄了《漢文典》。③ 《漢文典》側(cè)重于對(duì)文義、文法、修辭內(nèi)容的論述,關(guān)于文章流別、文體的討論較為薄弱,《史稿》則剛好彌補(bǔ)了這一缺陷。兩者是在同一學(xué)術(shù)思路下的內(nèi)容互補(bǔ),同為中學(xué)堂“中國(guó)文學(xué)”科教科書(shū)。④ 同樣作為國(guó)文教科書(shū),與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體例模式、結(jié)構(gòu)與內(nèi)容安排極為相似的還有劉師培( 1884—1919) 的《中國(guó)文學(xué)教科書(shū)》( 1906) 。《中國(guó)文學(xué)教科書(shū)》計(jì)劃編寫(xiě)十冊(cè)。在內(nèi)容安排上“先明小學(xué)之大綱,次分析字類,次討論句法章法篇法,次總論古今文體”⑤。
這種以“小學(xué)”為根基,包括經(jīng)學(xué)、史學(xué)、文章學(xué)在內(nèi)的“學(xué)術(shù)史”框架在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著述中相當(dāng)普遍。隨著“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興起,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學(xué)建設(shè)者倡導(dǎo)接受西方文學(xué)觀念,這種將小學(xué)、經(jīng)學(xué)等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體系納入文學(xué)史框架的情況才開(kāi)始改變。直到 1927 年鄭振鐸《文學(xué)大綱》問(wèn)世,才淘汰了傳統(tǒng)小學(xué)、經(jīng)學(xué)等非文學(xué)史內(nèi)容,文學(xué)史框架結(jié)構(gòu)基本確立。
( 二) 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另類”模式成因
近年來(lái),對(duì)于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另類”模式的成因,學(xué)界主要有以下幾種意見(jiàn): 首先,直接成因是近代教育改革的影響。隨著新學(xué)制、新學(xué)堂的建立以及新式國(guó)文教育的展開(kāi),以國(guó)文課教科書(shū)身份出現(xiàn)的“中國(guó)文學(xué)史”,既要滿足教改的“致用”目的,又要契合恢復(fù)“人倫道德”精神旨?xì)w,最終達(dá)到課程教育以中國(guó)固有之學(xué)為主,兼及西學(xué),實(shí)現(xiàn)“中體西用”。⑥ 其次,根本內(nèi)因在于對(duì)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體系的認(rèn)同與強(qiáng)調(diào)。近代教改下形成的“七科之學(xué)”中,“文學(xué)”一科包含了經(jīng)學(xué)、史學(xué)、理學(xué)、諸子學(xué)、掌故學(xué)、詞章學(xué),是由傳統(tǒng)“四部之學(xué)”衍生而來(lái)的。盡管課程設(shè)置是仿照西方、日本學(xué)制設(shè)定的,但“文學(xué)”一科并未改變中國(guó)固有的學(xué)術(shù)構(gòu)成。我們對(duì)西學(xué)的借鑒大多是制度層面,并未深及內(nèi)里。再次,編撰者自身的學(xué)術(shù)背景、知識(shí)體系構(gòu)成及文學(xué)史觀也有一定影響,來(lái)裕恂、劉師培、黃人具有良好的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功底,而后廣泛接觸西學(xué),能夠?qū)χ形鲗W(xué)術(shù)優(yōu)劣作出合理判斷與取舍。最后,作為“西學(xué)東漸”的產(chǎn)物,文學(xué)史本身就是“舶來(lái)品”。彼時(shí)西方、日本的文學(xué)史以文藝?yán)碚摗⑽膶W(xué)批評(píng)為主導(dǎo),但這種治史思路、文學(xué)史模式與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研究有明顯差異,因此不能照搬照抄。然而處于晚清中西學(xué)術(shù)交流的現(xiàn)實(shí)背景下,作為新式國(guó)文教育教科書(shū)的中國(guó)文學(xué)史編撰,又不可能走傳統(tǒng)目錄學(xué)的老路,因此必然要接受外來(lái)知識(shí)與經(jīng)驗(yàn)。關(guān)于“外來(lái)資源”對(duì)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編撰的影響,學(xué)界亦有討論。陳廣宏詳細(xì)梳理了黃人《中國(guó)文學(xué)史》對(duì)日本太田善男《文學(xué)概論》的吸收與改造,以太田善男為“中介”,對(duì) 19 世紀(jì)英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的吸納。① 朱首獻(xiàn)分析了晚清以來(lái)西方以進(jìn)化論、實(shí)證主義為理念的科學(xué)主義對(duì)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著作精神內(nèi)核、話語(yǔ)模式及價(jià)值維度的深刻影響,并指出由于科學(xué)主義與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不相適應(yīng),在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建構(gòu)過(guò)程中對(duì)西方科學(xué)主義的過(guò)度迷信與依賴,產(chǎn)生了迄今為止無(wú)法超越的學(xué)術(shù)瓶頸。② 溫慶新針對(duì)外來(lái)資源對(duì)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編撰的影響進(jìn)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他論述了日本笹川種郎《中國(guó)文學(xué)史》、遠(yuǎn)藤隆吉《中國(guó)哲學(xué)史》、坂本健一《日本風(fēng)俗史》、日本《漢文典》、赫德《辨學(xué)啟蒙》、赫胥黎《天演論》等西學(xué)著作對(duì)林傳甲《中國(guó)文學(xué)史》的影響,以及日本《漢文典》與來(lái)裕恂《中國(guó)文學(xué)史稿》的關(guān)系等,使我們對(duì)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對(duì)西方、日本外來(lái)經(jīng)驗(yàn)的借鑒與吸收有了一定認(rèn)識(shí)。③
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誕生于晚清中西交流的特殊背景下,作為“西學(xué)東漸”的產(chǎn)物,彼時(shí)西方、日本的文學(xué)觀念、文藝?yán)碚摕o(wú)疑對(duì)這一時(shí)期文學(xué)史的思維模式、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等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但應(yīng)明確的是,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仍以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為主導(dǎo)的“另類”模式,是近代學(xué)術(shù)變遷大勢(shì)之下,新舊學(xué)術(shù)體系相權(quán)衡保持國(guó)家民族文化特色的結(jié)果。這種集中西知識(shí)為一體的文學(xué)史,對(duì)外來(lái)資源的借鑒具有明顯的比較視野。以往的研究多關(guān)注西方文藝?yán)碚摗⑽膶W(xué)批評(píng)思想、同質(zhì)作品與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的關(guān)系、影響等,相對(duì)忽略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誕生的時(shí)勢(shì)背景、編撰目的以及模式的多方來(lái)源。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以新式國(guó)文課堂教科書(shū)身份存在。晚清新學(xué)制的設(shè)定、新式國(guó)文課程的安排基本參照鄰國(guó)日本,因此新式國(guó)文教科書(shū)的編撰也不免受其影響。其中同為“漢文教科書(shū)”的日本 “漢文典”的重要作用往往被學(xué)界忽視。“漢文典”仿照西方語(yǔ)法著作模式,也包含了傳統(tǒng)小學(xué)、文法、修辭、文章學(xué)在內(nèi)。以往學(xué)界多關(guān)注日本“漢文典”與清末漢語(yǔ)文法研究的關(guān)系及其漢語(yǔ)史意義。④ 深入發(fā)掘,便會(huì)發(fā)現(xiàn)“漢文典”與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編撰的密切關(guān)系。基于此,本文旨在說(shuō)明日本“漢文典”體例模式、內(nèi)容構(gòu)成及其實(shí)踐路徑如何對(duì)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編撰產(chǎn)生影響,進(jìn)而分析“漢文典”被接受的原因,這對(duì)厘清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另類”模式的多方來(lái)源具有重要意義。
二、日本“漢文典”體例模式及其實(shí)踐路徑
( 一) 日本“漢文典”體例模式與內(nèi)容構(gòu)成
日本自江戶時(shí)代便開(kāi)始通過(guò)蘭學(xué)⑤了解西方學(xué)術(shù)體系,明治時(shí)代實(shí)行文明開(kāi)化政策,廣泛接受西學(xué)。幕末、明治時(shí)期傳入日本的西語(yǔ)教科書(shū)及語(yǔ)法著作,多以“文典”為名,如《英吉利文典》《德意志文典》《法文典》《ビネヲ英文典》等。明治十年( 1877) ,大槻文彥解《中國(guó)文典》、金谷昭訓(xùn)點(diǎn)《大清文典》、①岡三慶著《漢文典》②問(wèn)世,這是日本學(xué)者最早以“文典”命名漢語(yǔ)語(yǔ)法著作。其中,岡三慶《漢文典》雖參照西洋語(yǔ)法,但仍舊延續(xù)了江戶以來(lái)漢語(yǔ)文言研究傳統(tǒng),詳細(xì)分析了文言虛字用法。在《漢文典》基礎(chǔ)上,岡三慶于明治二十年( 1887) 出版《岡氏之中國(guó)文典》,該書(shū)以日根尾《英文典》體系為參照,在日本首次建立了漢語(yǔ)文言語(yǔ)法體系。隨后,日本出現(xiàn)研究漢語(yǔ)文言的熱潮,這類著作基本以“漢文典”命名。總體來(lái)說(shuō),主要分為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 泰西語(yǔ)法系“漢文典”。這類“漢文典”參照西洋語(yǔ)法結(jié)構(gòu),以“品詞”理論為主線,包括詞法和句法兩部分,屬于純粹的語(yǔ)法研究著作。以岡三慶《岡氏之中國(guó)文典》( 1887) 為肇始,包括新樂(lè)金橘《中學(xué)漢文典》( 1900) 、《高等漢文典》( 1909) 、上田稔《漢文典》( 1901) 、廣池千九郎《漢文典》( 1905) ③。這其中廣池千九郎《漢文典》極具代表性,其《漢文典》既有詞論和句論,又包括對(duì)漢語(yǔ)性質(zhì)、漢語(yǔ)特征、漢文典內(nèi)涵的思考,并具有比較意識(shí)。這表明日本的文言研究已經(jīng)脫離江戶時(shí)期以來(lái)的虛字訓(xùn)詁研究,開(kāi)始進(jìn)入近代語(yǔ)法研究階段。
第二種模式: 傳統(tǒng)小學(xué)與語(yǔ)法結(jié)合系“漢文典”。這類“漢文典”“以資讀者鉆研古文”為目的,語(yǔ)法多被視為研習(xí)古文作文的工具。如豬狩幸之助《漢文典》( 1898) 、六盟館編輯所《漢文典表解》( 1905) 、中等教育學(xué)會(huì)《漢文典·表解細(xì)注》( 1912) 。這類模式的代表作是豬狩幸之助《漢文典》,該書(shū)借鑒了西方語(yǔ)法與中國(guó)傳統(tǒng)訓(xùn)詁學(xué)研究成果,被認(rèn)為是“傳統(tǒng)小學(xué)與漢語(yǔ)文言語(yǔ)法相結(jié)合的代表性著作”④。其“序論”部分為傳統(tǒng)文字、四聲、字音、音讀內(nèi)容; “附錄”部分是傳統(tǒng)音韻學(xué)內(nèi)容,主要介紹了日本《韻鏡》的研究情況,并詳細(xì)列出三十六字母的發(fā)音部位與發(fā)音方法、兩百零六韻、十六攝、《韻鏡》四十三轉(zhuǎn)等,還包括日本音韻研究史及意大利外交官 Volpicelli 所撰《古韻考》內(nèi)容。正文部分分為品詞篇、單文篇、復(fù)文篇、多義文字篇、同義文字篇,以語(yǔ)法知識(shí)為主。
第三種模式: 字法、句法、篇法、章法綜合系“漢文典”。以兒島獻(xiàn)吉郎《漢文典》( 1902) 、《續(xù)漢文典》( 1903) 為代表,包括八木龜三郎《漢文典表解》( 1907) 、普通講習(xí)會(huì)《漢文典表說(shuō)》( 1909) 、森慎一郎《新撰漢文典》( 1911) 。兒島獻(xiàn)吉郎《漢文典》分“文字典”和“文辭典”兩篇: “文字典”是傳統(tǒng)文字、音韻、訓(xùn)詁研究; “文辭典”著重分析十品詞、諸詞的關(guān)系及其位置種類。《續(xù)漢文典》分“文章典”“修辭典”兩篇: “文章典”論述了文章集字成句、集句成章的規(guī)則以及我國(guó)古典文章辨體之議論; “修辭典”以我國(guó)傳統(tǒng)修辭“文品”討論為主。兒島獻(xiàn)吉郎以古典學(xué)術(shù)體系為主,融合最新“語(yǔ)法”知識(shí),采用文字、文法、文學(xué)三位一體模式,這種綜合模式對(duì)日本及中國(guó)“漢文典”中國(guó)國(guó)文教科書(shū)編撰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由此可見(jiàn),日本學(xué)者對(duì)于“漢文典”的理解,與將西洋文典理解為純粹的語(yǔ)法著作不同。特別是以兒島獻(xiàn)吉郎《漢文典》為代表的綜合系“漢文典”,內(nèi)容遠(yuǎn)超出西洋文典范圍。其關(guān)于“文法” 內(nèi)涵的認(rèn)知明顯溢出西洋“Grammar”概念,此處的“文法”強(qiáng)調(diào)的是我國(guó)古代“言有序、言有物、言有章”的作文之法,以文章寫(xiě)作為最終旨?xì)w。
( 二) 日本“漢文典”對(duì)早期中國(guó)國(guó)文教科書(shū)編撰的影響
“漢文典”在日本流行之后,也為當(dāng)時(shí)留日的中國(guó)留學(xué)生所關(guān)注,并被迅速引介到中國(guó)。此時(shí)正值晚清教育改良之際,學(xué)校體系及課程設(shè)置參照日本學(xué)制,分為“普通”與“專門(mén)”之學(xué)。光緒二十九年( 1903) ,《奏定學(xué)堂章程》頒布,其中關(guān)于語(yǔ)言文字課程的“中國(guó)文學(xué)”科兼有讀寫(xiě)能力培養(yǎng)及基礎(chǔ)知識(shí)教育雙重功能。屬于“普通”教育的初等小學(xué)堂設(shè)“中國(guó)文字”科,主講動(dòng)字、靜字、虛字、實(shí)字區(qū)別,虛字實(shí)字聯(lián)綴之法以及積字成句之法。① 高等小學(xué)堂“中國(guó)文學(xué)”科多采古文選本以習(xí)古文、作文之法。至中學(xué)“中國(guó)文學(xué)”科“入學(xué)堂者年已漸長(zhǎng),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緩,首講文義、文法、作文,次講中國(guó)古今文章流別、文風(fēng)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關(guān)系處”②。中學(xué)堂與初級(jí)師范學(xué)堂學(xué)生學(xué)力相等,故師范學(xué)堂“中國(guó)文學(xué)”課程與之大致相同。
“普通”國(guó)文教育之后,按照《章程》,大學(xué)堂“中國(guó)文學(xué)門(mén)”為“專門(mén)”之學(xué)。主課設(shè)有: 文學(xué)研究法、《說(shuō)文》學(xué)、音韻學(xué)、歷代文章流別等。其中,“研究文學(xué)之要義”明確規(guī)定教學(xué)內(nèi)容: 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書(shū)、隸書(shū)、北朝書(shū)、唐以后正書(shū)之變遷; 古今音韻之變遷; 古今名義訓(xùn)詁之變遷; 古以治化為文、今以詞章為文關(guān)于世運(yùn)之升降; 修辭立誠(chéng)、辭達(dá)而已二語(yǔ)為文章之本; 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語(yǔ)為作文之法; 群經(jīng)文體; 東文文法; 文學(xué)與人事世道、國(guó)家、地理、世界考古、外交、學(xué)習(xí)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關(guān)系。③ 課程內(nèi)容涵蓋了傳統(tǒng)小學(xué)、修辭、文法、文體變遷、文章“義法”、文學(xué)與諸學(xué)科關(guān)系等多個(gè)方面,與中學(xué)堂、師范學(xué)堂“中國(guó)文學(xué)”科內(nèi)容有一定重合之處,屬于國(guó)文教育之“高階”。
隨著教改的實(shí)施,從基礎(chǔ)國(guó)文教育到專門(mén)“中國(guó)文學(xué)”科,都將“文法”設(shè)為必修課。此處的“文法”不僅包括來(lái)自西洋的詞類、句法結(jié)構(gòu)等新知的 Grammar,還有“‘備于古人之書(shū)’,以‘平易雅馴’ ‘清真雅正’為標(biāo)準(zhǔn),以古文‘義法’為旨?xì)w的作文之法”④。這與日本“漢文典”關(guān)于“文法”內(nèi)涵的理解一致。開(kāi)展“文法”教學(xué)的當(dāng)務(wù)之急是編撰教科書(shū),此時(shí)馬建忠的《馬氏文通》雖已問(wèn)世,但一直被教育界詬病“文規(guī)未備,不合教科”而備受冷落。而由鄰國(guó)日本引介而來(lái)的“漢文典”在此時(shí)頗受關(guān)注,對(duì)清末文法教學(xué)乃至國(guó)文教科書(shū)編撰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日本“漢文典”最初以譯著形式進(jìn)入清末學(xué)界。1902 年,王克昌翻譯豬狩幸之助《漢文典》,以《教科適用漢文典》為名由杭州東文學(xué)堂刊行。1905 年,丁永鑄翻譯兒島獻(xiàn)吉郎《漢文典》,以《國(guó)文典》為名由上海科學(xué)書(shū)局出版。1906 年,商務(wù)印書(shū)館編譯所編刊《中國(guó)文典》,此本包括“正文” 與“參證”兩部分。正文取兒島獻(xiàn)吉郎《漢文典》“十品辭”,融合《馬氏文通》例證,利用“漢文典”框架對(duì)《馬氏文通》進(jìn)行重組,以彌補(bǔ)《馬氏文通》于文法教學(xué)之多重弊端。同時(shí),我國(guó)學(xué)者也以日本 “漢文典”為藍(lán)本,編撰了一系列文典,如來(lái)裕恂《漢文典》( 1906) 、章士釗《中等國(guó)文典》( 1907) 、戴克敦《國(guó)文典》( 1912) 、俞明謙《國(guó)文典講義》( 1918) 。這類取法日本的“國(guó)文典”也折射出晚清學(xué)人對(duì)于“文典”的認(rèn)識(shí)和文法課程的設(shè)計(jì)。這其中,除日本“漢文典”譯著及章士釗《中等國(guó)文典》 ( 1907) 取西洋文典純語(yǔ)法著作模式外,來(lái)裕恂《漢文典》( 1906) 、戴克敦《國(guó)文典》( 1912) 、俞明謙《國(guó)文典講義》( 1918) 則在詞法、句法教學(xué)基礎(chǔ)上加入傳統(tǒng)文章學(xué)內(nèi)容。如戴克敦《國(guó)文典·修詞篇》第二章“篇章”論述“篇章之分類”,按照體裁和性質(zhì)( 理勝、氣勝、情勝、才勝、辭勝) 兩方面劃分文章種類; 第三章“章法”從起、承、轉(zhuǎn)、合四個(gè)方面論述文章作法。而學(xué)習(xí)日本綜合系模式“漢文典”最為徹底的來(lái)裕恂《漢文典》自不待言。⑤ 其實(shí)章士釗早年在日本實(shí)踐女校任教時(shí),便以桐城派古文學(xué)家姚鼐《古文辭類纂》為課本講授國(guó)文。《中等國(guó)文典》原定名《初等國(guó)文典》,是章氏的課程講義,僅有詞法內(nèi)容,但章氏認(rèn)為“文典不外乎詞性論,文章論兩部”,想必章氏有意在“詞法”教學(xué)之后講授文章寫(xiě)作內(nèi)容。1907 年,黃人在《中國(guó)文學(xué)史》“文典”一節(jié)中評(píng)價(jià)國(guó)內(nèi)文典如《馬氏文通》( 馬建忠作) 、《文字發(fā)凡》( 龍志澤作,一曰《中學(xué)文法教科書(shū)》) 、《漢文典》( 商務(wù)印書(shū)局本) 、《英文漢詁》( 嚴(yán)復(fù)作) 、《文學(xué)釋例》( 章絳作) 。1908 年,廣池千九郎來(lái)華考察,與時(shí)任學(xué)部左侍郎的嚴(yán)修就“中國(guó)文典”等問(wèn)題進(jìn)行交流。嚴(yán)修贈(zèng)予廣池三部中國(guó)文典,即馬建忠《馬氏文通》、來(lái)裕恂《漢文典》、龍志澤《文字發(fā)凡》。這些著作涵蓋了語(yǔ)法、修辭,文章、文學(xué)諸多內(nèi)容,可見(jiàn)在清末學(xué)人眼中,“文典”的內(nèi)涵不局限于語(yǔ)法教科書(shū),這種認(rèn)識(shí)與日本學(xué)者,特別是兒島獻(xiàn)吉郎基本一致。我國(guó)學(xué)人譯注、編撰的文典著作主要用于中小學(xué)堂及師范學(xué)堂“中國(guó)文學(xué)”科文法課程,改變了以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文章教學(xué)局面,為原本混沌的文章寫(xiě)作找到可以傳授的法則。自此,日本“漢文典”與清末新式國(guó)文教育的溝通正式連接,清末學(xué)人也在對(duì)日本“漢文典”的接受、吸收、批判過(guò)程中不斷汲取養(yǎng)分,將西方最新語(yǔ)法知識(shí)融入傳統(tǒng)詞章之學(xué)中,完成文字—文法—文章—文學(xué)模式的統(tǒng)一,最終推動(dòng)新式國(guó)文教育的展開(kāi),并實(shí)現(xiàn)文學(xué)視閾下中國(guó)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體系的近代轉(zhuǎn)型。
三、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對(duì)日本“漢文典”的接受與吸收
( 一) 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對(duì)日本“漢文典”之吸收
1. 日本“漢文典”與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之內(nèi)容構(gòu)成
按照《章程》規(guī)定,大學(xué)堂“中國(guó)文學(xué)”科仍以小學(xué)、修辭、文章、文學(xué)等傳統(tǒng)舊學(xué)為主,同時(shí)也強(qiáng)調(diào)文法。林傳甲《中國(guó)文學(xué)史》內(nèi)容安排完全根據(jù)“中國(guó)文學(xué)門(mén)”課程設(shè)置。黃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參照“中國(guó)文學(xué)門(mén)”課程設(shè)置。① 來(lái)裕恂的《漢文典》與《中國(guó)文學(xué)史稿》整體貫徹了《章程》基本要求。作為國(guó)文教育的“高階”,與中學(xué)堂文法教科書(shū)編撰深受日本“漢文典”影響情況相侔,這一時(shí)期的中國(guó)文學(xué)史編撰,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日本“漢文典”的影響。首先在內(nèi)容方面,文學(xué)史多處取法“漢文典”,以林傳甲《中國(guó)文學(xué)史》為例,詳見(jiàn)表 1:
林傳甲《中國(guó)文學(xué)史》所援引日本“漢文典”內(nèi)容主要集中在第五篇、第六篇、第七篇,以文法、修辭、文章學(xué)內(nèi)容為主。所援引的正是當(dāng)時(shí)已在清末學(xué)界有一定影響力的兒島獻(xiàn)吉郎《漢文典》《續(xù)漢文典》。來(lái)裕恂《漢文典》在內(nèi)容方面也多處取自兒島獻(xiàn)吉郎《漢文典》《續(xù)漢文典》,此處不贅述。來(lái)氏詳舉“中國(guó)四千年來(lái)之文字”,這種古典傾向?qū)嶋H也是受兒島獻(xiàn)吉郎影響。但應(yīng)該明確的是,清末學(xué)人在借鑒西方、日本文典編撰國(guó)文教科書(shū)的同時(shí)亦有自己的評(píng)價(jià)與思考。來(lái)裕恂在《漢文典》序言部分就談到了東西文典優(yōu)劣之處: “如涅氏《英文典》、大槻氏《廣日本文典》之精美詳備者也。而或以《馬氏文通》當(dāng)之。夫馬氏之書(shū),固為杰作,但文規(guī)未備,不合教科; 或又以日本文學(xué)家所著之《漢文典》當(dāng)之,然豬狩氏之《漢文典》、大槻文彥之《中國(guó)文典》、岡三慶之《漢文典》、兒島獻(xiàn)吉郎之《漢文典》,此皆以日文之品詞強(qiáng)一漢文,是未明中國(guó)文字之性質(zhì)。”①黃人指出,文典“其體例最明備者,如《馬氏文通》《文字發(fā)凡》《漢文典》《英文漢詁》《文學(xué)釋例》,皆能貫通中西,上下古今,而仍不適于普及者,則以陳義太高,措詞太雅。已有學(xué)識(shí)者讀之,誠(chéng)足以破拘墟之見(jiàn),得反隅之益; 若以供束發(fā)受書(shū)學(xué)子之用,終苦奧衍。蓋其條目雖詳明,而佐證仍深隱也”②。可見(jiàn),晚清學(xué)人對(duì)“漢文典”的借鑒是立足于本國(guó)國(guó)文教育的實(shí)際情況,其目的在于利用 “語(yǔ)法”對(duì)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體系加以改造,以普及國(guó)文。
2. 日本“漢文典”與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之體例模式
除內(nèi)容之外,日本“漢文典”體例結(jié)構(gòu)與模式對(duì)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編撰也有一定影響。林傳甲《中國(guó)文學(xué)史》前三篇為傳統(tǒng)小學(xué)內(nèi)容,分別是文字、音韻、訓(xùn)詁篇,兒島氏《漢文典》第一部分“文字典”也是小學(xué)文字、音韻、訓(xùn)詁內(nèi)容。不過(guò)《中國(guó)文學(xué)史》前三篇的側(cè)重點(diǎn)為“小學(xué)學(xué)術(shù)史”的演進(jìn),而《漢文典·文字典》側(cè)重于字形、字音、字義等具體知識(shí)的講解。《中國(guó)文學(xué)史》第五篇為文法修辭內(nèi)容、第六篇為章法篇法內(nèi)容,對(duì)應(yīng)《漢文典·文辭典》《續(xù)漢文典·修辭典》字法、句法、章法、篇法部分。《中國(guó)文學(xué)史》第七篇至十六篇關(guān)于文體劃分對(duì)應(yīng)《續(xù)漢文典·文章典》第六章“體裁上之分類·篇章”部分。劉師培明確指出《中國(guó)文學(xué)教科書(shū)》“先明小學(xué)之大綱,次分析字類,次討論句法章法篇法,次總論古今文體”之結(jié)構(gòu)安排,而這一體例結(jié)構(gòu)與兒島《漢文典》《續(xù)漢文典》文字典— 文辭典—文章典—修辭典結(jié)構(gòu)一致。日本“漢文典”由文字而文法,而文章,而文學(xué)( 文體變遷) 的思路已深深嵌入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中。
雖然“漢文典”綜合模式成熟于日本,但早在光緒二十六年( 1900) ,國(guó)內(nèi)署名為“仁和倚劍生” 的學(xué)者所編《教育指針》“編書(shū)方法”一節(jié)中便有明確的“漢文典”編撰設(shè)想: “尚有最要者,即編‘漢文典’是也。中國(guó)文理甚富,而文法則甚無(wú)定例。”“漢文典”內(nèi)容應(yīng)包含: “( 一) 講文字造作之原。今世地球文字分為三大類,一類是英法德連字,一類為日本交字,第三類便是中國(guó)積字。蓋中國(guó)造字之原起于六書(shū)……漢字須講明六書(shū),字法分名字、語(yǔ)字、詞字三類。( 二) 究明語(yǔ)詞用法,東文講明詞性,屬于文典之第二部。西國(guó)文典亦如之,大致分為字法句法兩種。( 三) 文典宜講明文章結(jié)構(gòu)之體裁。”①可見(jiàn)在作者看來(lái),“漢文典”應(yīng)包含三個(gè)層次: 文字、文法、文章。我國(guó)學(xué)者真正將這一設(shè)想貫徹執(zhí)行的是來(lái)裕恂。來(lái)裕恂《漢文典》首先將“地球文字分為三類,英、法、德、俄字皆切音,文取聯(lián)系; 日本取漢字,造和文; 中國(guó)文字肇端于形,致用以義,字字獨(dú)立,以輕重緩急長(zhǎng)短之語(yǔ)表意”②。論述字品: “東文講明詞性,屬于文典之第二部,西國(guó)文典亦如是,大致分字法、句法兩種。”③文章典: “中國(guó)自上古至三代,語(yǔ)言文字不甚相離,故能以詞見(jiàn)法。”④來(lái)裕恂遵循的正是“仁和倚劍生”提出的“漢文典”體例模式。“仁和倚劍生”在“漢文典”編法之后還指出“取材于諸史文苑傳、《文心雕龍》及諸家詩(shī)文集,可以創(chuàng)立一文學(xué)小史稿本,依文學(xué)史定例,再編文典”⑤。在他看來(lái),文學(xué)史是針對(duì)“漢文典”內(nèi)容的延伸,來(lái)裕恂稍后編撰的《中國(guó)文學(xué)史稿》正是基于此。
“仁和倚劍生”提出的“漢文典”模式與日本綜合系“漢文典”模式一致,這種模式究竟來(lái)源于何處? 目前還沒(méi)有確切的證據(jù)。其實(shí)早在明治十年,岡三慶作《漢文典》時(shí)便萌生了編寫(xiě)《岡氏之中國(guó)文典》的想法,并設(shè)想過(guò)范圍更為廣泛的“漢文典”,包括字學(xué)、韻學(xué)、辭學(xué)、文學(xué)四個(gè)方面,但限于時(shí)間和精力,當(dāng)時(shí)他只能在辭學(xué)方面有所作為。這種模式最早可追溯到日本國(guó)語(yǔ)學(xué)者大槻文彥的代表作《廣日本文典》( 1897) 。該著作被認(rèn)為是折合了日本“傳統(tǒng)國(guó)語(yǔ)學(xué)派”和“西洋文典模仿學(xué)派”的登頂之作,對(duì)日本國(guó)語(yǔ)乃至漢語(yǔ)語(yǔ)法研究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兒島獻(xiàn)吉郎在其《漢文典》“例言”中明確指出自己的寫(xiě)作動(dòng)機(jī)起于《廣日本文典》。來(lái)裕恂亦稱贊《廣日本文典》為“精美詳備者”。《廣日本文典》率先采用了“文字篇”“單語(yǔ)篇”“文章篇”三位一體模式,這也是“仁和倚劍生”提及的“東文文典”分部模式。這一模式隨后被日本學(xué)者及清末學(xué)者用于漢語(yǔ)文法研究與教學(xué)中,只不過(guò)《廣日本文典》和日本部分“漢文典”⑥中“文章典”強(qiáng)調(diào)的是句法結(jié)構(gòu),而其他日本學(xué)者和中國(guó)學(xué)者則根據(jù)漢文、國(guó)文教育的實(shí)際情況進(jìn)行本土化改造,變?yōu)橄底殖删洹⑾稻涑善奈恼伦鞣āR詢簫u獻(xiàn)吉郎《漢文典》《續(xù)漢文典》為代表的日本“漢文典”正迎合了我國(guó)教育界關(guān)于“漢文典”編撰的訴求,因此被晚清學(xué)界廣泛借鑒用以編撰國(guó)文教科書(shū),對(duì)此前紛繁復(fù)雜的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體系進(jìn)行了簡(jiǎn)約化、實(shí)用化改造。
( 二) 日本“漢文典”影響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編撰之原因
在晚清中西交流的背景下,文學(xué)史編撰引入“外來(lái)資源”是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的主動(dòng)革新,與其他外來(lái)資源在清末中國(guó)接受程度不同的是,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對(duì)日本“漢文典”的接受與吸收具有普適性,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gè)方面:
1. 基于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體系的繼承與發(fā)展
日本“漢文典”在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編撰過(guò)程中能夠被廣泛接受,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漢文典”模式根植于日本漢學(xué),與中國(guó)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體系具有同質(zhì)性。日本自古以來(lái)深受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影響,整個(gè)江戶時(shí)代尤以漢學(xué)作為學(xué)術(shù)研究的主流,很多學(xué)者漢學(xué)功底極深。進(jìn)入明治時(shí)代,西方知識(shí)體系給日本社會(huì)造成強(qiáng)烈沖擊,致使日本本土的學(xué)術(shù)研究與思維模式發(fā)生變化,西學(xué)開(kāi)始成為主流。這種情況下,基于對(duì)漢學(xué)的保護(hù),許多學(xué)者積極投身到漢學(xué)研究中來(lái),并引進(jìn)西方學(xué)術(shù)體系,對(duì)傳統(tǒng)漢學(xué)進(jìn)行改良。日本著名國(guó)語(yǔ)學(xué)家大槻文彥有著深厚的漢學(xué)背景。① 1875 年,大槻文彥奉命編撰日本大型詞典《言海》②,其中涉及的和、漢、洋書(shū)籍超過(guò)八百余部,大槻氏充分掌握了三國(guó)文法特征,這為《廣日本文典》綜合系文典模式的建立鑒定了基礎(chǔ)。隨后將這種綜合模式用于漢文研究的兒島獻(xiàn)吉郎,出身漢學(xué)世家,早年畢業(yè)于東京大學(xué)古典講習(xí)科③,后擔(dān)任京城帝國(guó)大學(xué)漢文科主任教授。兒島獻(xiàn)吉郎以中國(guó)文學(xué)史研究而聞名,先后著有《中國(guó)文學(xué)史綱》《中國(guó)文學(xué)史( 古代篇) 》《中國(guó)文學(xué)考》《中國(guó)文學(xué)雜考》《中國(guó)文學(xué)概論》等著作,對(duì)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研究頗深。他在撰寫(xiě)《漢文典》《續(xù)漢文典》前已經(jīng)讀過(guò)涅氏《英文典》、大槻氏《廣日本文典》、馬建忠《馬氏文通》、豬狩氏《漢文典》,對(duì)中西日“文典”模式及內(nèi)容有了深入了解。兒島獻(xiàn)吉郎憑借深厚的漢學(xué)功底,以中國(guó)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體系為基礎(chǔ),引入西方最近“語(yǔ)法”知識(shí),簡(jiǎn)化以往復(fù)雜的漢文教學(xué)。明治時(shí)期,西學(xué)的大量涌入致使日本的漢學(xué)研究受到強(qiáng)烈沖擊,這與晚清社會(huì)受西學(xué)影響,出現(xiàn)一味追求西學(xué)、否定中學(xué)的熱潮相似。面對(duì)這種情況,出于保護(hù)“舊學(xué)”,繼承與發(fā)展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的共同目的,中日兩國(guó)學(xué)者需要利用西學(xué)改良舊學(xué),因此他們關(guān)于“漢文典”內(nèi)容構(gòu)成及體例模式的選擇達(dá)到時(shí)空一致的默契。這種模式正是基于近代學(xué)術(shù)變革以及保存舊學(xué)、普及國(guó)文需求的一種必然選擇。
2. 基于“開(kāi)啟民智”的教育致用目的
“漢文典”在日本形成編撰熱潮,與日本長(zhǎng)期以來(lái)重視“漢文”教育有很大關(guān)系。當(dāng)時(shí)日本正規(guī)學(xué)校教育“漢文”課堂中,“漢文法”是一門(mén)先行的基礎(chǔ)必修課。中等教育已經(jīng)將“漢文法”納入正規(guī)師范教育體制中。因此,其客觀上刺激了漢學(xué)復(fù)興與“漢文典”編撰。“漢文典”借鑒外來(lái)資源,為傳統(tǒng)漢文寫(xiě)作找到可以教授的法則,使得傳統(tǒng)文章學(xué)得以在近代學(xué)術(shù)變革中找到突破口,具有開(kāi)啟民智、普及漢文之作用。 “開(kāi)啟民智、普及國(guó)文”也正是晚清教育改革的出發(fā)點(diǎn)。晚清學(xué)人積極呼吁重視“文法”的重要性,并參照“文典”體例模式編撰教科書(shū)。林傳甲在《中國(guó)文學(xué)史》( 1904) “序”中稱: “或課余合諸君子之力,撰《中國(guó)文典》,為練習(xí)文法之用,亦教員之義務(wù),師范必需之課本也……更欲編輯《中國(guó)初等小學(xué)文典》《中國(guó)高等小學(xué)文典》《中國(guó)中等大文典》《中國(guó)高等大文典》,皆教科必需之課本。”④黃人不但肯定“文典”對(duì)于文學(xué)研究的重要性,更強(qiáng)調(diào)了“文典”對(duì)于教育普及、政令授受之作用。他稱: “文典一稱文譜,或即謂之文法,所以示組織文字之規(guī)則者也。其用與倫理學(xué)相表里; 而尤為國(guó)語(yǔ)學(xué)之進(jìn)階。今日世界諸國(guó),凡有文學(xué)者,莫不有文典,非特為文學(xué)之用也。一切形上形下之學(xué),皆賴以傳達(dá)。國(guó)家而無(wú)文典,則教育上之授受、政治上之教令,皆不能普及,故文典者,使國(guó)民得普及知識(shí)之要素也。”①在黃人看來(lái),中國(guó)的文學(xué)研究雖歷史悠久、內(nèi)容廣博,但并非真正的文學(xué)研究,主要原因則是無(wú)“章則”。他認(rèn)為文學(xué)“不通”主要是“凡此皆無(wú)文典之故”。他同時(shí)反思了東西文典“貫通中西,上下古今”之長(zhǎng)處,“陳義太高,措詞太雅”之弊端,在編纂《中國(guó)文學(xué)史》時(shí)引入“文典”概念,將文學(xué)研究與“文典”模式相結(jié)合,條分縷析,為傳統(tǒng)文學(xué)史編撰找出了新的路徑模式。持相同觀點(diǎn)的還有劉師培,他認(rèn)為: “中國(guó)無(wú)文典,此中文之一大缺點(diǎn)也。今欲教育普及,當(dāng)以編文典為第一義。予嘗謂文典與法典并重。無(wú)法典之國(guó),必為無(wú)政治之國(guó); 無(wú)文典之國(guó),即為無(wú)教育之國(guó)。中國(guó)并此二者而無(wú)之,此其所以上無(wú)政、下無(wú)學(xué)也。如以編文典為別例,則日本之初,亦曷嘗有文典哉? 是在隨時(shí)變通耳。”②來(lái)裕恂對(duì)日本“漢文典”認(rèn)識(shí)比較深入,并受其啟發(fā)“爰不揣梼昧,以泰東西各國(guó)文典之體,詳舉中國(guó)四千年來(lái)之文字,疆而正之,縷而晰之,示國(guó)民以程途,使通國(guó)無(wú)不識(shí)字之人,無(wú)不讀書(shū)之人。由此以保存國(guó)粹,倘亦古人之所不予棄也”③。日本取法西洋,通過(guò)注入最新“語(yǔ)法”知識(shí)以彌補(bǔ)傳統(tǒng)漢文教育無(wú)“法”可依的缺陷,使傳統(tǒng)文章寫(xiě)作得以有法可循,進(jìn)而普及漢文教育,這與新式國(guó)文教育追求“致用”的教育目的一拍即合。
3. 基于國(guó)學(xué)基本知識(shí)學(xué)習(xí)的實(shí)用性考量
作為東亞最早向西方學(xué)習(xí)的國(guó)家,日本最早完成現(xiàn)代轉(zhuǎn)型。當(dāng)時(shí)晚清社會(huì)處于急劇動(dòng)蕩時(shí)期,晚清政府迫于形勢(shì)壓力決定學(xué)習(xí)鄰國(guó)日本的經(jīng)驗(yàn),但在教育方針上始終堅(jiān)持以“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為指導(dǎo)思想。頒布于 1898 年的總理衙門(mén)《籌議京師大學(xué)堂章程》就明確提出: “考東西各國(guó),無(wú)論何等學(xué)校,斷未有盡舍本國(guó)之學(xué)而能講他國(guó)之學(xué)者; 亦未有絕不通本國(guó)之學(xué)而能通他國(guó)之學(xué)者。”④然而隨著西方新思想、新名詞的大量涌入,民族文化及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受到強(qiáng)烈沖擊,頗有“厭家雞愛(ài)野鶩”之風(fēng)氣。一些有志之士及“教改”推動(dòng)者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保持國(guó)家民族文化獨(dú)立的重要性。鄰國(guó)日本早有蘭學(xué)研究傳統(tǒng),對(duì)西學(xué)并不陌生,在協(xié)調(diào)西學(xué)知識(shí)體系與傳統(tǒng)舊學(xué)方面有著豐富的經(jīng)驗(yàn)。且“日本學(xué)校雖皆習(xí)西文,而實(shí)以其本國(guó)文及漢文為重,所授功課皆譯成本國(guó)文者,其各類品類各物皆訂有本國(guó)名目,并不假?gòu)轿魑摹G椰F(xiàn)其出洋之人,皆學(xué)業(yè)有成之人,否亦必學(xué)有根柢之人。故能化裁西學(xué)而不為西學(xué)所化。”⑤日本善于運(yùn)用西學(xué)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本國(guó)傳統(tǒng)舊學(xué),因此成為晚清社會(huì)學(xué)習(xí)的楷模。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并非研究性著作,而是新型國(guó)文教育教科用書(shū)。作為教科書(shū),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內(nèi)容的實(shí)用性和學(xué)生的接受度,這就決定了文學(xué)史編撰不可能采用純學(xué)術(shù)史編撰模式。當(dāng)時(shí)的文學(xué)史編撰苦于沒(méi)有適合國(guó)文教育實(shí)際的參考材料,西方的文藝?yán)碚撆c我國(guó)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體系存在著極大的不相容性。因此,借鑒鄰國(guó)日本的國(guó)文教科書(shū)“漢文典”,無(wú)疑是最經(jīng)濟(jì)實(shí)用的選擇。況且日本本身受中國(guó)文化影響頗深,又有治理西學(xué)的經(jīng)驗(yàn),其“漢文典”以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為主導(dǎo),兼及西學(xué),無(wú)疑為晚清新型國(guó)文教育展開(kāi)及中國(guó)文學(xué)史編撰提供了借鑒。
四、余論
“文學(xué)史”這一舶來(lái)品,在中國(guó),其誕生是伴隨著學(xué)科建立,以教科書(shū)形式出現(xiàn)的。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兼有技能訓(xùn)練與知識(shí)普及之用途,既要兼顧舶來(lái)的西方文藝?yán)碚撆c觀念,又要將中國(guó)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融入到新學(xué)框架下,以實(shí)現(xiàn)中西、新舊、古今學(xué)術(shù)的溝通。作為近代學(xué)術(shù)體系變遷的重要標(biāo)志,早期中國(guó)文學(xué)史有著明顯的“外來(lái)資源”痕跡,接受了西方史學(xué)特別是文學(xué)史、哲學(xué)史等社會(huì)科學(xué)知識(shí),具有初步的中西學(xué)術(shù)融合態(tài)勢(shì)。但從根本上來(lái)說(shuō),西學(xué)知識(shí)的引入是為傳統(tǒng)“文學(xué)”學(xué)術(shù)體系改良服務(wù)的,在這種內(nèi)驅(qū)力作用下,對(duì)日本“漢文典”體例模式及內(nèi)容進(jìn)行吸收與改良,借助外動(dòng)力使得從“文法”到“文學(xué)”的進(jìn)階得以順利展開(kāi),為中國(guó)文學(xué)史編撰與新型國(guó)文教育展開(kāi)找到了合理出口,進(jìn)而達(dá)到“開(kāi)啟民智”的教育目的。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jiàn)問(wèn)題 >
SCI常見(jiàn)問(wèn)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