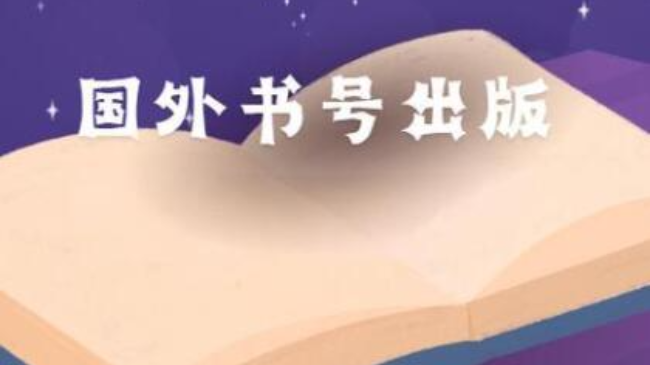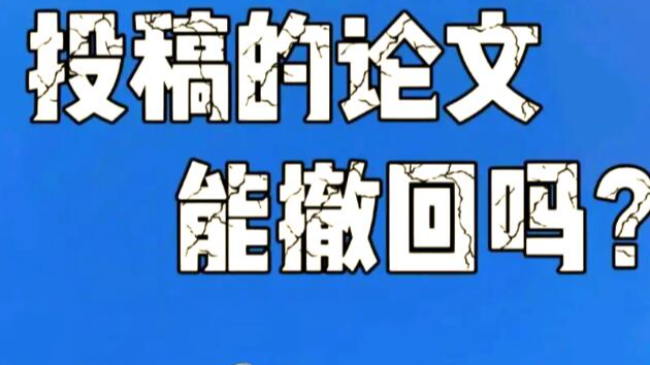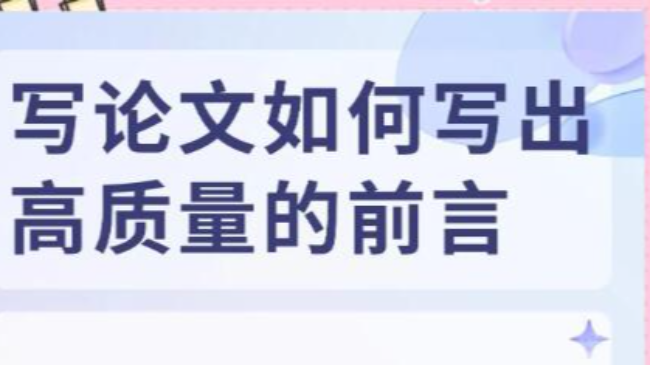云計算背景下著作權(quán)法的修改探討
本文作者:張惠彬 單位:西南政法大學(xué)知識產(chǎn)權(quán)研究中心
在商業(yè)方面,云計算的服務(wù)模式主要有三種:基礎(chǔ)設(shè)施即服務(wù)(Infrastructure-as-a-Service,以下簡稱“IaaS”)、平臺即服務(wù)(Platform-as-a-Service,以下簡稱“PaaS”)、軟件即服務(wù)(Software-as-a-Service,以下簡稱“SaaS”)。[4]IaaS,指的是使用者可透過向云計算服務(wù)提供者租用的方式,使用處理器、儲存容量、網(wǎng)絡(luò)等基礎(chǔ)的運算資源,不需自行購買硬件及基礎(chǔ)設(shè)施。PaaS,指用戶直接租用云計算服務(wù)提供者的程序開發(fā)平臺和操作系統(tǒng)平臺,借由其專業(yè)的服務(wù)器來進行運算及儲存,讓各地的開發(fā)人員能同時透過平臺來撰寫程序、開發(fā)軟件。SaaS,指的是云計算服務(wù)提供者透過網(wǎng)絡(luò)提供商使用軟件的服務(wù)。與傳統(tǒng)的軟件使用相比,SaaS不僅減少或取消了軟件的授權(quán)費用,且服務(wù)商將應(yīng)用軟件部署在同一的服務(wù)器上,免除了最終用戶的服務(wù)器硬件、網(wǎng)絡(luò)設(shè)備和軟件升級維護的支出。
在法律方面,美國近期發(fā)生的案件也說明,云計算作為一種獨特的商業(yè)活動,其所涉及的案件分布在各法律領(lǐng)域。目前云計算的服務(wù)類型包括了美國《數(shù)字千年版權(quán)法》第512條(K)款(1)項中列舉的僅提供緩存、信息儲存空間、搜索以及鏈接等技術(shù)服務(wù)。此時,云計算服務(wù)提供者在網(wǎng)絡(luò)信息交流中處于消極中立的地位,在用戶利用其服務(wù)實施侵權(quán)行為的情況下,服務(wù)提供者主要承擔間接責任或可援用“避風港原則”進行抗辯。同時,云計算服務(wù)還包括允許用戶在線使用商業(yè)軟件的服務(wù),在這類型服務(wù)中,云計算服務(wù)提供者處于積極主動的地位,假如其所提供的軟件沒有合法來源,服務(wù)提供者就有可能處于侵權(quán)人的地位,承擔直接侵權(quán)責任。綜上所述,云計算服務(wù)實質(zhì)上是時下主流的網(wǎng)絡(luò)服務(wù)的綜合模式,云計算服務(wù)提供者在本質(zhì)上屬于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5]
波詭云譎:云計算對傳統(tǒng)著作權(quán)保護之挑戰(zhàn)
從著作權(quán)法制發(fā)展的歷史觀察,著作權(quán)法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一直與技術(shù)緊密關(guān)聯(lián)。可以說,著作權(quán)的保護起源于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展,而著作權(quán)法制的演進與修正,亦與科學(xué)技術(shù)的進步息息相關(guān)。然而,與科學(xué)技術(shù)的進步相比,著作權(quán)法律制度未必能跟得上科學(xué)技術(shù)的腳步,以至于每一項新技術(shù)出現(xiàn)時,著作權(quán)法律制度便面臨著這樣那樣的挑戰(zhàn)。云計算的出現(xiàn)也不例外,其對傳統(tǒng)著作權(quán)法的專有權(quán)利、授權(quán)合同、合理使用等制度帶來了巨大的挑戰(zhàn)。
(一)云計算引導(dǎo)著作權(quán)專有權(quán)利制度的革命。傳統(tǒng)上,著作權(quán)法通過賦予權(quán)利人一系列著作財產(chǎn)權(quán)和著作人身權(quán)來達到維護權(quán)利人經(jīng)濟利益之目的。其中,發(fā)行權(quán)和出租權(quán)是著作權(quán)法中重要的財產(chǎn)權(quán)。在云計算時代,信息不再依附在書、光盤等有體的媒介上,而是儲存在網(wǎng)絡(luò)的虛擬空間中。消費者通過注冊、付費、憑密碼獲得進入這個虛擬空間的資格,甚至密碼還須經(jīng)由特定的IP地址或捆綁的電子設(shè)備才能進入該虛擬空間,在付費期間獲得對這些作品的使用權(quán)。這種方式的使用具有很大的節(jié)能環(huán)保的好處,因其避免了大量的光盤等介質(zhì)對環(huán)境的危害。通過這種方式的應(yīng)用和推廣,不得不深思傳統(tǒng)發(fā)行權(quán)和出租權(quán)在云計算服務(wù)中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云計算已使得傳統(tǒng)著作權(quán)商品(如書、計算機軟件光盤等)從所有權(quán)的讓與轉(zhuǎn)化為使用權(quán)的授權(quán),消費者再也買不到這些作品的有體物所有權(quán)。對于這些作品,消費者也不再有絕對掌控權(quán),而是在付費使用的期限內(nèi)擁有法定的使用權(quán)。
(二)云計算促使著作權(quán)授權(quán)合同制度的改革。在以往的軟件授權(quán)合同,權(quán)利人往往以特定的條款約束和監(jiān)測用戶的使用。例如微軟在其Office2003軟件協(xié)議中就列明:用戶僅可在一臺個人計算機或其他設(shè)備上安裝和使用一個軟件副本,并需擁有由微軟提供的軟件許可證,才能在網(wǎng)上獲得升級軟件的權(quán)利。在云計算中,由于軟件的使用都是云計算服務(wù)提供者的服務(wù)器上進行的,因此相關(guān)軟件有時須在服務(wù)提供者的服務(wù)器上進行復(fù)制方可運行,這種復(fù)制容易產(chǎn)生著作權(quán)法上的爭議。在用戶使用由服務(wù)提供者自身開發(fā)、擁有著作權(quán)的軟件之情形下,產(chǎn)生著作權(quán)爭議的機概率較小。因軟件授權(quán)的相關(guān)規(guī)定通常已包含于授權(quán)合同中。但是,假如用戶是使用第三方所提供的軟件,且用戶與該第三方的授權(quán)合同未專門針對云計算環(huán)境設(shè)立,則用戶在使用該軟件時在服務(wù)提供者服務(wù)器上的產(chǎn)生復(fù)制件,恐有侵犯著作權(quán)的嫌疑。因此,如何制定和完善計算機軟件授權(quán)合同以適應(yīng)云計算環(huán)境下的需要,有效降低著作權(quán)糾紛,不得不引起云計算業(yè)者的重視。
(三)云計算引發(fā)著作權(quán)合理使用制度的變革。在云計算等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興起之后,著作權(quán)合理使用制度面臨著重大的影響。一方面,著作權(quán)法上的作品與制品都會以數(shù)字化的形式在世界范圍內(nèi)傳輸。用戶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只要通過手上的電子數(shù)碼設(shè)備就可獲得所要使用的作品與制品。如果任由這種方式泛濫,即使是個人性質(zhì)的使用,也會顛覆權(quán)利人的市場。另一方面,為防止作品被非法使用,權(quán)利人開始采用技術(shù)措施,禁止使用者任意接觸、復(fù)制、發(fā)行、傳播和修改作品。應(yīng)當說,在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環(huán)境下,對權(quán)利人采用的技術(shù)措施加以保護是必要的。然而,在云計算的環(huán)境下,提供服務(wù)的大多是技術(shù)實力雄厚的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且服務(wù)都以網(wǎng)絡(luò)的途徑提供。一般用戶付費之后連作品的原件或復(fù)制品都掌控不了,更不用談如何去破解這類技術(shù)措施了。這種方式不僅限制了作品的使用方式,且使得公眾原有的對于作品的合理使用空間,在云計算服務(wù)提供者強大的保護技術(shù)的控制下,完全不可能進行。
云霓之望:云計算與我國著作權(quán)法修改
當前,中國“云”可以說是異常火熱,北京、上海、廣州、重慶等城市相繼推出了云計算發(fā)展的產(chǎn)業(yè)計劃。因此,雖然云計算在我國引起的著作權(quán)糾紛尚未出現(xiàn),但為保護著作權(quán)人的利益和推進云計算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我國著作權(quán)法必須有所回應(yīng),及早為“云”籌謀。國家版權(quán)局于2012年3月公布了著作權(quán)法的第三次修改草案并征求公眾意見。從著作權(quán)法修改草案的內(nèi)容看,其一方面體現(xiàn)了立法者力求與時俱進的良苦用心,在很多方面做了一些突破性的規(guī)定;另一方面也存在許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不能很好地應(yīng)對云計算等新技術(shù)對著作權(quán)保護的挑戰(zhàn)。
第一,在專有權(quán)利部分。草案重新對復(fù)制權(quán)進行了定義:復(fù)制權(quán),即以印刷、復(fù)印、錄制、翻拍以及數(shù)字化等任何方式將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權(quán)利。但對于“數(shù)字化等任何方式”的復(fù)制是否包括了“臨時復(fù)制”,版權(quán)局在有關(guān)草案的修改說明中并未進行闡述。假如是包括“臨時復(fù)制”,那么按照這一規(guī)定,任何云計算用戶未經(jīng)授權(quán)使用計算機軟件,都會由于軟件在運行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進入服務(wù)提供者的服務(wù)器中構(gòu)成復(fù)制,陷入著作權(quán)的侵權(quán)之虞。對此,筆者認為草案的規(guī)定不符合我國國情,不具備現(xiàn)實操作性。因為“臨時復(fù)制”僅僅是一種客觀的技術(shù)現(xiàn)象,具有暫時性、附帶性,沒有獨立的“經(jīng)濟價值”。[6]如在享受云計算的服務(wù)當中,用戶每次在網(wǎng)上運行軟件時,都不可避免地在服務(wù)提供者的服務(wù)器內(nèi)產(chǎn)生“臨時復(fù)制”,這種復(fù)制作為計算機處理數(shù)據(jù)過程中的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是用戶在網(wǎng)上瀏覽作品時不自覺發(fā)生的,絕大多數(shù)用戶根本沒有意識到“臨時復(fù)制”的存在。
第二,在合理使用制度部分。草案第40條沿襲了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規(guī)則主義”立法模式,規(guī)定了十二項合理使用的法定事由。這種模式的立法的最大弊端就是有可能排除一些應(yīng)當屬于合理使用的行為。隨著科技的發(fā)展,人們對合理使用的認識與判斷隨時會改變,要在立法上囊括現(xiàn)實中各種合理使用的情形是不可能做到的。這一立法方法也暗示了立法者唯理建構(gòu)主義的理想,其內(nèi)在的邏輯是,立法者可以洞察現(xiàn)實社會的一切。這是一種憑借理性就能重構(gòu)社會的立場,然而,它在近代的實施證明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它保留了很多人類理性不及的領(lǐng)域。因此,建議我國立法采用“規(guī)則主義”與“因素主義”相結(jié)合的模式,在規(guī)定常見的合理使用法定事項的前提下,補充規(guī)定抽象的原則,讓法院在個案中可做彈性認定。
第三,在“避風港原則”部分。草案第69條明確規(guī)定了提供純技術(shù)服務(wù)的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不承擔與著作權(quán)和相關(guān)權(quán)有關(guān)的審查義務(wù),并概要規(guī)定了通知移除程序。這部分規(guī)定與《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條例》基本一致。至于有音樂界人士質(zhì)疑的,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不承擔審查義務(wù)是助長了盜版的氣焰,筆者認為,不承擔審查義務(wù)并不意味著網(wǎng)絡(luò)侵權(quán)行為就會愈加猖獗,因為條文明確規(guī)定了“單純技術(shù)服務(wù)”這個前提條件,如果任何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越過了這條紅線,一旦涉及內(nèi)容服務(wù),那么第69條將不再適用。并且強求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具有審查義務(wù),在目前的技術(shù)上也是不具備操作性的。如在MP3tunes.com案中,被告提供給用戶免費的在線音樂儲存空間,允許用戶在該空間上存放成千上萬首歌曲,如果要對每一首歌曲是否具有合法的授權(quán)進行核查,那么就連谷歌這種互聯(lián)網(wǎng)巨頭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另外,草案第69條對于“知道”一詞的表述與《侵權(quán)責任法》第36條有所不同。《著作權(quán)法》修改草案采用的表述是“知道”或“應(yīng)當知道”,而《侵權(quán)責任法》第36條采用的只是“知道”,這種表述不一的情況,容易導(dǎo)致司法實踐中混淆,亟須從立法層面上予以解決。
在云計算時代,由于技術(shù)的便利導(dǎo)致著作權(quán)人處于極為脆弱的狀態(tài),需通過著作權(quán)法作進一步的規(guī)范。然而,法律若是對于著作權(quán)進行周全的保護,又可能約束科技的發(fā)展,限制公眾合理使用的空間。因此,立法者須認知到其間的利益平衡,在保護權(quán)利人利益、維護科技發(fā)展以及公眾合理使用等方面作出均衡的考慮。[8]此外,網(wǎng)絡(luò)世界法律的執(zhí)行還需與技術(shù)相呼應(yīng)。勞倫斯•萊斯格教授提出“代碼就是法律(codeislaw)”的概念。[8]他認為,在網(wǎng)絡(luò)上要建立制度和規(guī)范,除政府工作外,網(wǎng)絡(luò)上的程式建構(gòu)本身在相當程度上就決定了網(wǎng)絡(luò)的運作模式,從事網(wǎng)絡(luò)相關(guān)工作的技術(shù)人員實質(zhì)上就是網(wǎng)絡(luò)的立法者,他們這么做除依循國家的法律之外,還受商業(yè)機制和約定俗成的規(guī)范影響。如果將“代碼就是法律”的觀念發(fā)揮到極致,就是借由代碼本身來達到法律所要的目的與功效。現(xiàn)在處理網(wǎng)絡(luò)上法律爭議時,大多用外顯的方式去處理,造成政府、企業(yè)或民眾要應(yīng)對這樣的方式往往付出沉重的成本。實際上,有許多科技帶來的保護問題在技術(shù)層面解決,可能會來得更直接與徹底,社會成本也較小,有些爭議自然就不會發(fā)生。
本文html鏈接: http://www.suonuo77.com/qkh/28918.html